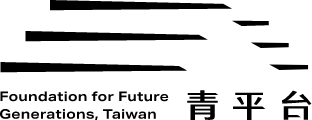【政論】小鴨、療癒、禽流感


(基隆海洋文化中心前的黃色小鴨,周克任攝影,2014.2.1)
看!黃色小鴨耶!
等等,怎麼會是這樣?
可愛?
我相信,如果在我們眼前的是這隻鴨子,應該不可能引起2013年九月開始,從南到北,綜貫整個台灣,如同流感般地感染台灣人的黃色小鴨風潮,不論小孩大人,驚嘆有之、興奮有之,嘲諷有之,失望有之,甚至連原創者弗洛倫泰因·霍夫曼(Florentijn Hofman)可能再怎樣也想不到的版權爭議也發生,而在2013年的最後一天,以戲劇化的爆裂,為同樣刺激的台灣這一年紛紛擾擾收尾。
一個朋友說,2013年歲末小鴨爆頭讓他驚愕之餘開懷大笑,「果然,這隻鴨是有療癒效果的!」一群人哈哈笑開,我倒是覺得李國修說得沒錯:「人,才是殘酷的,人總是看到別人發生不幸的事而覺得好笑」。我們如此地期待這隻鴨,這隻鴨卻又這樣地回應我們,不知道那些在基隆碼頭邊、指頭比著V字拍照的小朋友,會有多失望?而大老遠從台北跑來,以為可以稍解天龍國裡、卑微討生活的苦鬱的上班族,這下子療癒不成反倒是更加鬱卒。
為什麼這隻香港人稱為「巨鴨」,台灣人稱之為「小鴨」的充氣製品可以有療癒效果?一個敏感的朋友早在九月小鴨還在高雄時,便提到了「高雄的鴨,跟香港的鴨,感覺不同,或者,高雄的鴨沒有給我那種療癒的感覺。」的確,我也這麼認為。
霍夫曼自謂黃色小鴨的創作理念是簡單、平靜,希望帶給人們同樣單純的快樂與幸福。我想,這或許就是這作品傳說中的「療癒效果」吧?但,若真如霍夫曼的構想,那麼,這隻鴨到哪裡,不都該有同樣的效果?否則,這豈不是一個失敗
的作品?2007年以來,這隻小鴨的各個尺寸不一的分身,在歐洲、紐澳、日本、香港都蔚為風潮,怎會到台灣就吃憋?荷蘭人與荷蘭鴨真的到台灣就沒輒?我聯想到1662被鄭成功趕跑的荷蘭人,不,應該說是上一回席捲台灣的荷蘭文化。
黃色小鴨與台灣的羈絆正可以從十七世紀開始講起。某些學術觀點將十七世紀視為「近代」的起點。當時,君主政治逐漸獨立於宗教之外,資產階級興起,民主思想也開始萌芽。雖然宗教力量仍是歐洲社會的主宰,但科學精神逐漸昂揚,藝術則是更世俗化、更具運動性、情感表現的巴洛克時期。勇於掠奪的歐洲人開始向外擴張,來到的亞洲,不斷累積的殖民資產成了我們眼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濫觴。而台灣,進入世界史正是從近代歐洲人的海外拓殖開始。
今天,這隻荷蘭鴨子來到亞洲,我們首先是看到它靜靜地泊在香港九龍尖沙咀海港城海運大廈前,在其身後是環維多利亞灣、高聳的商業大樓群。我們彷彿看到一隻感性的小鴨,用以飽滿的生命力、勇敢地突破在資本主義冷酷理性的精神環境,這種巨大的對比反差,不下於十七世紀巴洛克對古典均衡的挑戰,更具體地再一次展示西歐文明在東方社會裡的異質性。
這反差的地景,正形成傅柯所謂「異質空間」(異托邦,heterotopias):「那些存在於既有空間中的特有空間,其功能異於甚且與其它空間相反」。講白一點,小鴨處於此處,有著格格不入的奇異,而且是一種「純潔童趣」進入「高壓競爭」的氛圍衝突,不論是現場觀看還是透過媒體畫面,有別於孩童的興奮,對一個成年的觀看者而言,黃色小鴨是一種呼喚,喚起心中被工作打壓到幾乎殆盡的單純與平靜;黃色小鴨是一種反射,彷彿自己就像這隻無辜的小鴨,在商場中被強權環伺,而仍然錚錚定定地做著自己。
啊~牠懂我!我因此被療癒。
並非「巨大」而帶來療癒,也不全然是單純的設計風格、暖調色彩帶來療癒。反而是在「比自身的巨大卻在更巨大的面前顯示的渺小」,給人產生同理的映射、感性的移情。這是亞洲金融中心香港的鴨子,成功的都市童話,也是接下來台灣對小鴨到訪的期待。
但,到了台灣卻不一樣了。高雄的鴨子在地方政府近年強力營造的觀光勝地愛河灣頭展出一個月,吸引參觀人潮達390萬人次;而後桃園的鴨子在交通不便的桃園新屋埤塘,連同受損後重置於岸邊陸上展出約半個月,人數達161萬;最後,基隆的鴨子在煤灰酸雨瀰漫的基隆碼頭展出50天,期間破裂而後起死回生,參觀人數達267萬人次。三個當地政府公布的這幾個數字不知如何計算得來?除非許多遊客可從水面方向前來參觀,否則以三處當地鄰近道路面積、交通載具的運量,要胃納這樣的人潮運輸,實在難以想像。但台灣媒體禀持著向來不質疑政府數據的態度,盡情地為政府代言。純真、平靜的原創理念在媒體報導中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官方「亞洲最大、世界第二」、「讓全世界都看得到埤塘」、「基隆與國際接軌」炫富式的口號。就在官方熱切地宣傳「特色文化」、也毫不掩飾宣傳自己的政績時,網路酸民也將酸味發散到極致,KUSO版百出,嘲諷挖苦在所多有;反觀商家最務實,台灣人做過路財、並非仿冒的「概念雷同」、一窩蜂搶進的生意手腕再次發揮到淋漓盡致,不但在遍地的小鴨商品中看到,我們也能看到在「沒有小鴨」的其他城市裡,看到大家如何沾點鴨毛多少撈一點。這段期間,台灣出現的巨型鴨類,至少有在高雄展場結合鋼鐵人造型的「鋼鐵鴨」、新屋展場被警方取締的「紅面薑母鴨」、優游在花蓮縣鯉魚潭受政府保護的紅面番鴨、彰化花壇鄉公所製作的含淚保麗龍鴨……等等。至於同時期另一個熱門動物,貓熊,也可作夥相伴:腦筋動得快的彰化二林代安宮、台南安南區土城正統鹿耳門聖母廟,都將小鴨與熊貓並列,為信徒提供同時到位的服務。甚至沒有水也沒關係,台南走馬瀨農場小鴨與熊貓同臺,台中神岡的潭雅神綠園道有黃色巨鴨、市中心勤美綠園道也可擺出成群白色小鴨,基隆某殯葬業者更在大片山坡地以十一萬只風車陣列出小鴨地景。誰說政府沒效率?這幾個月的期間,地方政府與民間同步為著拼觀光,沾小鴨之光賺錢,終於使得全國都感染了小鴨禽流感。
禽流感的現象再次驗證了台灣社會不改多元的特色,每個人、每個部門都可找以取得自己的意義,自己High自個兒樂,自證自成但卻也自我封閉。藝術是一種交流的形式,透過藝術品,可以超越文字與算式所無法傳遞的感性,與他人產生共鳴。但在商業化後,或者是另一個已經氾濫的名詞,「文創商品」,藝術感性的意義消退,價值被化約只剩下產銷利益。不論這利益是個人獨佔還是全民均沾,這筆觀光財一開始便削弱了小鴨的價值。有誰會在賣聚氯乙烯的小鴨時,讓自己釋放出來,看到自身的童趣在市場經濟裡一同被交換掉?在官媒合作的嘉年華會裡,有誰會去懷疑:真的能在這樣的活動裡找到幸福?他們說這是一種文創產業,那麼,文化呢?
可別像網路的批評,多少帶有鄙夷的口氣,不自覺地流露出以荷蘭正宗洋文化為尚、為標準的心態,來貶抑我們政客與商人的「台客味」。如果我們在香港的小鴨裡,透過環境映襯,重新掌握了霍夫曼透過小鴨這個藝術品所傳遞給我們的感動與療癒,那麼,脫離作者的台灣鴨,難道不能以藝術本身的存在,對映著台灣獨有的場域,重新產生意義?
有,這隻小鴨帶來的可能是個「世紀末的療癒」
還記得2006、07年嗎?當年台灣社會在政爭高峰裡,所幸有王建民在紐約洋基的表現,給了台灣人一扇可以透口氣、療癒的窗;而2008年,同樣的政爭,沒有了王建民的台灣卻仍幸運地有了魏德聖的海角七號,國民電影消弭了台灣人藍綠的躁動,開始了小確幸的年代;到了2013年,小鴨沖淡了民調低落的當局帶給人民的苦悶,歲末的爆炸更是一吐政爭怨氣。有小鴨的台灣是可以興奮的,即使這興奮彷彿只是爛泥地裡的小花,得來好似容易,卻也不容易。這種卑微的興奮其實是一種世紀末的療癒,不明說,但好像人人都心知肚明:我們在「明天應該不會更好」的狀況裡的苦中作樂。
但是,逐漸喪失希望的療癒與安寧,是這小鴨所僅能給我們的啟示,以及台灣人內心集體困局的反映表徵嗎?還有沒有更多?還有沒有別的?我們怎麼能讓這隻可愛的鴨子以一個天使姿態,揭發我們內心失意之後,曉諭我們世紀末的到來,而我們卻無力作為?我們再走一次小鴨的路線,由南到北,發現了小鴨行跡的另一個線索,告別。
高雄市民知道,這次來光榮碼頭看小鴨,以後可能再也沒有幾次機會了。日治時代以桁樑結構築成的13號碼頭送過日軍前進南方的軍需物資,迎接過在南洋叢林裡九死一生歸來的台籍日本兵;開赴中國的船上,士兵拿著槍掃射跳水逃兵也不願參與中國內戰台灣人;碼頭後來改名為「光榮」,不變的是在此處搭船到金門服役的年輕人,以及在碼頭邊含淚送別的女友,對映著碼頭邊、高雄市最短的一條路,英雄路。所謂的「英雄氣短,兒女情長」啊!這一切都要告別了,高市府即將在此興建流行音樂中心,一個市民可以聚會的大型廣場空間即將消失,連同其上百年來的故事一併抹去,小鴨帶著市民對這空間告別、對這家鄉的記憶告別。
來到了桃園,隔壁池塘裡的日韓藝術家的地景作品,並沒有受到桃園縣民多少注目,反而是不遠處航空城自由經濟示範區裡,拆屋徵地的抗爭才是當地大事。為著這史無前例、尚無具體營運計畫的航空城,桃園縣政府將十七公頃的埤塘以區段徵收的方式,填平埤塘造建地。縣政府一方面消滅埤塘,卻又一方面宣稱要將桃園縣所有埤塘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候選地,民眾休閒與生態環境教育的場址。小鴨帶著充滿疑惑的桃園鄉親,告別埤塘文化、告別涵養土地的水文生態,也告別了理性的、民主的公共政策邏輯。
小鴨最後一站來到了基隆,告別的對象正是身旁基隆港西岸碼頭倉庫。1934年落成的碼頭倉庫,無言地迎接過殖民帝國的皇子,也送走殖民帝國的軍隊,而後又迎接來台灣鎮壓民變的21軍、國共內戰敗退的國民黨軍民。這八十個年頭來,這是個外人在此檢疫、分發,台人在此告別家鄉,天涯浪跡的「台灣的嘴巴」(李乾朗教授語),已在近日拆除。而來基隆看小鴨的民眾何其有幸,見證了這個碼頭最後的光彩,告別了將目光投向大海的時代。基隆的領導菁英早已沒有海洋壯志,回頭轉向內地台北,乞求那個不見得對基隆有利,反可能抽乾基隆生命力的大台北捷運。
基隆不是沒有建設,反而是建設過多。上上下下的人行、車行陸橋,是一種給車方便給人不方便的城市規劃。穿越的陸橋割裂了社區的完整,刺破了住宅的寧靜。但這些犧牲又換得了什麼?城市蕭條後,港埠相關設施不再是城市的引擎而是包袱,當城市人口白天都在鄰近的台北時,這個城市何以要犧牲具有再生潛力的工業遺址,而去招徠一個超越其消費人口量能的大賣場?倘若這城市的規劃者仍將繼續以「省個幾分鐘到台北」的捷運為訴求,將「通勤」看得比「安居」來的重要,不啻是將城市定義為只是晚上睡覺的地方而已?基隆人真正需要的是一個安居的生活,想想青壯年在台北工作時,留在家裡的老人與小孩過的是怎樣的生活?文教、社福、醫療、公園、社區交通是否充足?基隆,向山向海,宜居宜家,根本不需要粉紅色的鎖管、黃色的小鴨來錦上添花,更何用在小鴨之後緊接著上台的「咕咕雞」?
讓我們再看一眼這隻黃色小鴨,這是隻有獨特鴨嘴紋、獨特美學意義的台灣鴨。牠彷彿成了台灣,灰僕僕的臉龐刻劃出年華老去的歲月,黯然的眼神告別著昔日的光榮,透著兩個港都的風霜與紅土埤塘的風雨。曾給我們歡樂、療癒的小鴨,消風垂倒後宛如在問我們:在牠闔眼之後,台灣能不能告別這世紀末的氛圍,向著海洋,找到出口,破浪而行?
 念此際
念此際
你已靜靜入睡
留我們未完的一切
留給這世界
這世界
我仍體切地踏著
而已是你底夢境了.....
──鄭愁予,錯誤
作者:李重志(青平台基金會研究專員)
文章出處:《台灣建築》,期222,20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