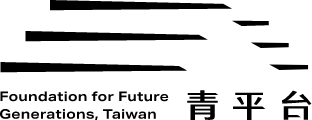轉型正義過程中法律的功能與作用(一)

 依學者施正鋒的歸納,就學術的範疇而言,轉型正義至少包含法學(刑法、人權)、政治哲學(正義論)、以及比較政治學(民主化)等三個專門領域,甚至於有「轉型學」(transitology)的用法(施正鋒,2007:4)。事實上,從歷史學及人類學觀點切入者亦不乏其人(施正鋒,2006;吳豪人,2012:67~93)[1]。而根據統計,截至2013年10月,美國威斯康星大學「轉型正義資料庫」收錄的相關文獻已近2500份[2]。2001年,國際性非政府組織「轉型正義國際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簡稱 ICTJ)成立,專門致力於該問題的研究與實踐。2007年3月,《國際轉型正義期刊》(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itional Justice)正式創刊,成為該領域的第一本國際性學術雜誌。因此,說轉型正義這個議題是當前國際學術界最具爭議性的議題之一,應不為過。
依學者施正鋒的歸納,就學術的範疇而言,轉型正義至少包含法學(刑法、人權)、政治哲學(正義論)、以及比較政治學(民主化)等三個專門領域,甚至於有「轉型學」(transitology)的用法(施正鋒,2007:4)。事實上,從歷史學及人類學觀點切入者亦不乏其人(施正鋒,2006;吳豪人,2012:67~93)[1]。而根據統計,截至2013年10月,美國威斯康星大學「轉型正義資料庫」收錄的相關文獻已近2500份[2]。2001年,國際性非政府組織「轉型正義國際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簡稱 ICTJ)成立,專門致力於該問題的研究與實踐。2007年3月,《國際轉型正義期刊》(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ransitional Justice)正式創刊,成為該領域的第一本國際性學術雜誌。因此,說轉型正義這個議題是當前國際學術界最具爭議性的議題之一,應不為過。
本文研究之目的乃係藉由闡述:一、近年來國際法理論與實務的快速發展,及二、法學界對法律功能的更清楚瞭解這兩個面向,來試圖論證法律在轉型正義過程中所應該扮演的角色,可能比之前相關的討論中所認知的更為重要及關鍵。
就前者而言,2004年8月,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向聯合國安理會,提交了名為「衝突中和衝突後社會的法治和轉型正義」的報告[3]。說明在冷戰後由於國際刑法、國際人權法及國際人道法學術上的迅速發展,以及「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ICTY)、「盧安達國際刑事法庭」(ICTR)等各種臨時國際刑事法庭及混合刑事法庭的豐富實務經驗,以及其所立下及累積的典範與標準,在對於轉型正義過程中,刑事追訴的重要性與正當性已有了更為普遍的共識。
就後者而言,過去對刑罰目的的思考,主要仍以應報思想及預防思想為主,但在上個世紀九○年代後期,一種新的理論形成,對法律系統在社會中所擔當的功能有了更為精確的認知與掌握,因此,嘗試透過其觀點,對於法律在轉型正義中所能產生的作用,可以有比起之前更為清楚的認識與評價。
根據轉型正義國際中心(ICTJ)的普遍定義,轉型正義過程是指「為了回應系統化與廣泛的違反人權作為時,所採取的一切方式、手段、制度及機制」。這些程序程和機制既可以是司法性質的,也可以是非司法性質的,其中包括起訴、賠償、真相調查、機構改革和人事淨化(lustration)。事實上,早在1995年美國和平研究中心的Neil Kritz 就出版了三大本資料豐富,針對各國處理轉型正義所採取的各種措施與機制,以及其後續發生的影響與評價有詳盡敘述之專著(Kritz, 1995)。故轉型正義過程中採取的措施及機制,依各面臨轉型正義國家之客觀政、經、社環境需要或障礙,應依循不同的的路徑與模式。
總言之,絕大多數學者都同意,轉型正義過程中可採用的機制是多元化和多重性的,最主要是為了因應不同客觀條件與階段的需要。以刑事處罰、賠償性懲罰或者歷史正義的方式,是為了對強化民主制度以及提高社會中相互間的信任。因為司法程序、行為調查委員會、補償、公開道歉或者達成一種共享的歷史觀等等機制,都是足以影響社會大眾行為,促進轉型正義目標的工具(Hazan, 2006: 23-24)。
聯合國秘書長的報告中也強調,「在進行轉型正義時,戰略必須是全面的,包括兼顧起訴個人、賠償、尋求真相、改革機構、審查和革職的問題,或這些行動的任何適當組合」。
甚至於,如果只有單純的審判,補助受害者、真相調查委員會,或更替與淨化的機制,將不會對社會和解有長期重大影響,對民主化的促進更是效果不彰。而是應該同時、平行地針對結構性不平等進行改革,並改善社會中受壓迫族群之基本物質需求換句話說,只有透過持續地、衡平地與合併不同措施的作法,才能對民主制度有長遠的影響( Hayner,2002)。
然而,對於最核心的問題,也是最難回答的問題,即何種措施、哪項機制乃轉型正義得以成功的最基本必要條件,學界顯然至今仍未有共識。本文即試著以轉型正義理論與實踐發展至今所累積的研究成果,及豐富的實務經驗,論證刑事追訴應被視為是所有轉型正義工程中,必須採取的奠基措施。
剛開始時,轉型正義的討論主要集中在其與民主化及民主之間的關係,尤其受到杭廷頓(Huntington)針對1970和 1980年代有關南歐、拉丁美洲及東歐的第三波民主討論的著作影響極大(Huntington,1991).。而1991年冷戰結束後,為數眾多的民主國家誕生,更促成了許多的研究方法的擴展,也更增加了對轉型正義對民主化民主鞏固和民主的品質的衝擊的關注,因此,對轉型正義的發展階段的劃分,常與民主的發展階段相聯結。
相對於其他政治學者習慣以民主發展階段,做為轉型正義的階段劃分標準,Ruti Teitel 對轉型正義的時期分界,即主要以國際法的發展及其實際上的適用做為標準(Teitel, 2003: 69-94)。第一階段為「戰後轉型正義」,將「紐倫堡大審」及「東京大審」視為是人類歷史上,首次國家主權在與對嚴重的人權侵害進行訴追發生衝突時,必須退居次位,也就是一國的政治與軍事領導人必須為其犯行負起刑責。而藉此也為之後許多在人權發展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審判程序,如經聯合國安理會決議設立的1993年「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ICTY)[4]、1994年「盧安達國際刑事法庭」(ICTR) [5]、2003年6月6日與柬埔寨(Kambocha)[6],在2002年1月12日和獅子山(Sierra Leone)[7]簽訂協定,成立柬埔寨刑庭與獅子山刑事法院,以及波西尼亞、東帝汶、科索沃、黎巴嫩等地設立的各種混合刑事法庭所立下及累積的典範與標準。第二個階段則是「後冷戰的轉型正義」,其特色是對於過往不義政權的處理,國際法與內國法之間開始進行整合,另一種新趨勢是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設置。第三階段則是以在1998年通過,2002年生效的國際刑事法院規約(又稱羅馬規約)及海牙國際刑事法院的成立,做為往後對體系不義處理的共通程序與模式。
Teitel的分類標準與方法,無疑地對轉型正義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啟發效果。因為在論及成功的轉型正義過程中,刑事追訴是否為必要條件時,法、政學者不是採取否定的看法,例如Huntington(1991:267-268)及Ackerman(1992:69),更多則是模稜兩可式的看法:認為在應報理論的影響下,國家在道義上必須盡力以刑法追究過去威權政權侵害人權的嚴重罪行,否則形同受害人的人性尊嚴仍然繼續受到蔑視,也無以伸張正義、法治等立憲法秩序的規範價值;但同時又質疑,應報的正義觀往往會被報復性的情緒所挾持,其實踐可能有害於鞏固民主所必要的社會和解。另一方面,在一般預防理論的影響下,認為以刑罰權來處理轉型正義,有助於嚇阻、避免侵犯人權的政府犯罪再度發生;不過,又擔心其所欲追求的預防、嚇阻目的,是否具有真正必要性(蘇俊雄,2007:68)。
吾人不否認,的確,如何處理轉型正義在理念上與實踐上規範價值的兩難,無疑是轉型正義之規範理論的重要課題(Teitel, 2009: 2044-48)。但採取否定看法的學者一方面多屬較早之前的論者,根本未目睹到聯合國自1993年ICTY以降所取得的實際上重大成就,且另一方面過度將焦點集中於拉丁美洲或東歐[8]等新興民主國家之內國法院無法讓人心存期待,或實際上令人失望的表現上,以致得出此一結論。但經歷過聯合國在國際人權法實踐上顯著的成果,東歐後期民主化的表現後,原本採取質疑立場的學者亦逐漸變少,愈來愈多論者支持「國家應該在可能的範圍內追懲舊政權之犯罪行為」此一規範立場的趨勢(蘇俊雄,2007:68;Hesse & Post, 1999: 13, 15)。
例如,一般懷疑論者總以犯罪之追訴、審判與處罰,恐有違罪刑法定主義及其所衍生的刑法不溯及既往原則。然而,對於嚴重侵害人權、凌虐人道之罪行的嚴重性,不僅國際法上已有公約明文要求內國與國際刑法對其所為訴究不受時效限制[9]。其次,常被舉為反例的:匈牙利的憲法法院曾以違反法治國形式正義為由,判定該等對延長犯罪追訴時等效溯及性的立法是違憲的,也漸顯牽強。第一、匈牙利憲法法院認為違憲的部分僅指「非嚴重罪行」,換言之,對「嚴重罪行」部分是承認其合憲性的。第二、德國也遇過同樣的質疑,但該國聯邦憲法法院認為射殺穿越邊界者的行為是無可忍受的不法行為,基於實質正義的理由,取消追訴時效之規定,並未違反回溯禁止原則。最後,該判決被告到提歐洲人權法院(EGMR),EGMR在2001年3月判決認定為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的判決,並無抵觸歐洲人權公約第七條第一項關於罪刑法定主義及禁止溯及既往的規定,理由在於雖然是無可否認的法治國原則之一,但仍容許其例外之存在,因為東德這種射殺穿越邊境者的駭人聽聞行為,乃係對於生命權這個在國際人權法的價值天平上最高法益的侵害,不受歐洲人權公約第七條第一項(罪刑法定原則)的保護(EGMR Urteil vom 22.03.2001)。歐洲人權法院的判決對所有歐盟會員國具有法律上之拘束力,匈牙利在加入歐盟之後,當然也受該判決的效力拘束。
就此,對舊政權的刑事訴追與法治國原則間的緊張關係,應該被視為已有定論,無須再以此例進行無謂的爭論。學界意見這樣的轉變趨勢,也讓人對於未來在轉型正義過程中採取刑事追訴手段時,有較多積極正面的期待。再加上以下所述及的近年來對法律功能的新認知,應該可以更肯定司法程序對轉型正義的正面貢獻。
接轉型正義過程中法律的功能與作用(二)
照片來源:小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