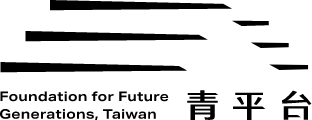專訪寇延丁:從小城女工,到行腳千里的中國異議份子(轉載自女人迷:womany.net)

讀者投書迷人來稿,專訪寇延丁,一路投身社會運動的她,說到自身對社運的看法:「這世界變得更好或更壞,永遠取決於願意付出代價做出改變的少數人。」
作者|李奕萱(就讀台大外文系)
「我乾了,您隨意。」是寇延丁在青平台主辦的「釀壺民主釘子酒」座談會的開頭標題,這句話從寇延丁的口中說出,溫婉和緩,彷彿揭示了她在訴說理念時的態度。
寇延丁是中國公益人士,推行基層民主、自下而上的自組織,在香港雨傘革命期間,曾因認識相關人士而以「顛覆國家」之罪入獄。近來,在臺灣已有一年餘的她行腳四方:參與白屯媽祖遶境、以腳踏車繞臺,旅途中,她不斷向臺灣的人們講述理念:「不了解中國不符合臺灣利益。」呼籲大眾關注中國的議題。
在女性相對少見與弱勢的參政舞台上,寇延丁的形象相當特別,她自稱「溫和建設者」,不強求以說理來說服人,而是溫和地用故事來推廣她的理念,並且直接將理念付諸行動。
塑膠瓶裝著的自釀火龍果酒
初遇寇延丁(而後都稱她為寇姐)的第一個印象,是她的樸素。清癯的面孔,短而灰白的髮絲,她身材纖細,穿著輕便,像是下一秒要開始長征的運動員。她說話的聲音溫婉秀雅,徐緩而沈穩,發音端正,像是個中文老師。
才剛見面,寇姐就熱情招待我們她釀的酒。不似平常裝在玻璃瓶的酒,寇姐的酒用塑膠瓶裝著,她在中國家中習慣用瓷罈來釀酒,但到了臺灣後,沒有那樣的工具,因此就改以隨手可及的瓶子來釀酒。她帶來的酒是顏色豔麗的紫紅色火龍果酒,鮮亮的色彩彷彿要把透明的杯子染上一層迷人的紅,但那紅卻不張牙舞爪,而是靜靜地、溫柔地影響身邊的顏色。(推薦閱讀:用音樂感動社會的快閃運動:風雨生信心,傻是我們的氣魄)

寇延丁在座談會中準備自釀火龍果酒與米酒,與大家分享。 攝影/李奕萱
火龍果酒入口滑順,帶著水果的酸甜和酒精淺淺的苦澀,就像色彩一般怡人。「我釀過好多種酒,香蕉不太適合,芒果雖然本身很好吃,但釀起酒來就還好。」寇姐說,一邊在留下淺淺一層火龍果酒的杯子裡斟上淡白色的米酒,白色的米酒沖開了鮮紅的火龍果酒,先是像兩股不同的絲線互相編織,接著融為一體,變成了更溫柔的桃紅色,上面漂浮著一粒粒柔軟的米。她興奮地說:「你看這顏色,這時候的顏色最漂亮了。」
釀酒與以酒會友,這倒影了寇姐影響他人的做法:用最舒服、最輕鬆地方法,以一個朋友的態度,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在對等的關係下告訴別人她的看法。

火龍果酒與米酒混合的桃紅色。 攝影/李奕萱
意外下崗,投身公益
沒有一個人天生就是倡議者,然而人生中經常會有某個機緣,完完全全地帶著一個人往他從未想過的路走去。
寇姐出生於 1965 年,教育讓她就像身邊大多數的人一樣,相信中國應該要解放全世界其他三分之二的人口,相信政府,相信體制。長大以後,她陸續做過幾個工作,結了婚,有了孩子,日子平順。然而,在 1996 年,她發現自己工作的紙箱廠中,廠長假造發票,而她對這件事的告發卻換來了自己的下崗(中國特有名詞,意指在中國企業機構改革中失去工作,仍隸屬於原單位卻沒有工資)。禍不單行,在那之後,寇姐與丈夫離了婚,成為下崗的單親母親。(推薦閱讀:11歲開始做公益!沈芯菱:「人生就是一場溫柔小革命」)

寇延丁在座談會中認真看著紀錄片《上訪》,片中紀錄了抗議不公平遭遇卻被迫害的中國人。 攝影/李奕萱
接下來的生活並不簡單,然而難受的還包含了自己原先認知的破滅。原先安身於體制內的她開始對中國的政府與社會產生困惑,這樣的困惑迫使她重新去建立一個判斷事情的基準,逐漸讓寇姐走上了自己所沒想過的路。
1993 年,寇姐因為工作調動而接觸到殘障美術家,並開始嘗試推廣他們的藝術,無意之中,就成為了中國最早推廣殘障美術家的人。下崗後,寇姐除了嘗試新工作與寫作投稿外,更是越來越投入公益的行動:在 2005 年,她創辦了殘障美術家推廣公益組織「北京手牽手文化交流中心」,在 2008 年四川地震後,更是毅然投入救災,是當地唯一一個在做青少年長期救助的團體。
「在這個時候,我主要投入的有兩個面向:公益,還有自組織建立。」不單只是給需要幫助的人魚吃,寇姐希望能夠給這些需要幫助的人釣竿:透過建立公益自組織,讓有相同目的、需求的人組織起來,獨立運作。她相信這種自下而上的組織不只能夠幫助組織內的人,也可以幫助穩定中國現階段的結構與價值,甚至在未來國家面臨危難之時,這樣的公民組織與思考能力也能夠維持國家秩序。
除了公益組織外,寇姐還做了不少串連社會資源的工作,幫助留學歸來的「海龜(中國用語,從海外留學歸國的人)」將美國的「議事規則」帶入鄉村,並將這種基層民主嘗試記錄在《可操作的民主》一書中。《可操作的民主》不只得到民間組織高度認同,也因為裡頭的議事規則推廣而引來政府採購,用在城市治理的改革。(推薦閱讀:泰緬邊境公益之旅:離開他以後,我遇見了全世界)
在寇姐持續推動自組織和基層民主的過程中,她陸續結識香港佔領中環發起人陳健民、臺灣民進黨簡錫堦、海外民運人士王丹、吾爾開希等人,結果沒想到,因為這樣的關係,她成了第一個因「顛覆國家」而入獄的公益人士。
128 天入獄與 128 天健行
寇姐一直以來的所作所為,都是希望能藉由公益服務來組織社會、自下而上建設社會,她完全沒想過自己會因為「顛覆國家」而被捕。在 128 天的監禁中,她受到了嚴密監控,連在監房裡要移動、要去廁所都受到控管。無止盡的審問從寇姐的家庭到公益行動,再到她的私人交往,毫不放過。審訊者無時無刻都提醒著寇姐:「我們隨時都可以把妳拉出去槍斃。」
「你可以說我為國家做的事情是自作多情,但你們認為我想要顛覆國家也是自作多情。」難以接受這樣的罪名,寇姐曾經這樣告訴審訊者。
「中國監獄有個辦法叫『坐板兒』。」寇姐描述當時的審訊方法:在沒有靠背的座椅上一直直挺挺坐著。這樣的方法讓人的腰椎、脊椎、膝蓋、踝關節和肌肉通通退化,消化系統也停止運作。在這樣摧殘人的審訊與監禁中,許多熬不過的人不是精神崩潰了,就是身體垮了。但寇姐活了下來,128 天後,她離開監獄,改成在家中受控管。
那時候寇姐的身體極差,現在也相當纖瘦的寇姐只有 47 公斤,而那時的她足足比現在還瘦了 10 公斤,她說那時走路都像是用飄的。她很害怕自己會死掉,一次感冒都要 4、50 天才能好,咳一下就渾身疼。
在她被抓走的一年後,雖然身體狀況不見好轉,寇姊仍毅然決定以步行離家,抗議警察對她的行動限制,於是她開始了 128 天的耐力行走。沒想到這一走,她身體反而好轉。這奠下了她未來運動的習慣,也讓她開始以毅行來作為一個對抗體制的方式。
在寇姐接受訪問的那天,她一路從大坪林騎腳踏車到西門,騎了一個小時,但她絲毫不見疲態,反而神采奕奕。有許多投身政治的人會因為工作而失去健康,不過寇姐卻是以健康的身體來支持她的工作,也許正因為如此,她才能在不論運動上或參政上,都成為一個走得遠、走得久的毅行者。(推薦閱讀:志工筆記:我們付出不是為了得到,他們給我的永遠更多)

寇延丁出外健行的模樣。 圖片來源/寇延丁
為了孩子而努力的母親
直到今天,女性在參政上依然趨於弱勢,全球均然。2016 年日內瓦對女性議員做的研究報告中,女性議員全球比例是 23.3%,中國人民大會裡面的女性代表比例為 23.7%,即便在有了第一任女性總統的臺灣,女性立委的比例也是低於半數的 38%,這個數字甚至已經高於全世界大多數國家。在這樣的狀況下,寇姐以一個偏於陰性氣質的形象投入政治這點格外耐人尋味。
問起有關女性參政的事情,寇姐提到了兩個故事。第一個是南斯拉夫內戰時生還者的故事,描述那時候的女人經常為了一個牛肉玉米罐頭而讓人擺佈幾小時,而那些女人大多都是「絕望的母親」。另一個故事則出自影響她最大的一本書《黃禍(中國作家王力雄著)》,在書中,出現在男主角身邊的三個女人在末日中雖然各有定位,但卻一一邁入死亡。寇姐說:「雖然男主角是一個拯救世界的神,但他卻救不了自己身邊的女人。」
在現代中國,甚至臺灣,女性參政依然有很多都是被逼出來的,也許為了被捕的丈夫被捕,也許為了保護兒女的權益,也許為了抗爭自己或身邊的人權利受損。然而她們出面後經常會受到責難,像是李明哲的妻子李淨瑜就多次被控訴是在為自己的政治鋪路。在參政後,有些女性會刻意讓自己偏向社會價值中的陽性氣質,以得到大眾的認同與信任。(推薦閱讀:【性別觀察】「李明哲,我以你為榮」李淨瑜救夫為何成了政治陰謀?)
寇姐沒有刻意去改變什麼,對於寇姐來說,她的確就只是個「絕望的母親」。為了自己的孩子,也為了她在公益組織裡頭見過的許許多多個孩子,希望自己能夠給他們一個更好的生存機會,因此她選擇站了出來,維持自己原本的個性與態度,用這樣的方式來走出自己的路。
溫柔不強迫的溝通者

演講時寇姐溫柔親切而堅定。 攝影/ 李奕萱
「社會變革是一個極其漫長的過程,總是從極少極少數人開始的。可能只有 0.001% 甚至更少⋯⋯一旦到了 20%,社會變革的大勢已經動起來了——永遠不要考慮那 80%,他們永遠都是被動的。這個世界變得更好或者更壞,永遠取決於願意付出代價做出改變的少數人。」--寇延丁
雖然寇姐一直致力於改善社會、發揮自身影響力,她卻認為自己並不是個擅於說服的人。她熱愛自由,深怕自己會不小心強勢地讓別人接受自己的想法。也許正是因為如此,她總是試著以最舒適、最體諒的方法來告訴人她的想法,用行動力來為自己理念做最好的背書。(推薦閱讀:《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你必須參與,最壞的年代才可能變成最好的年代)
在中國時,她的溝通方法是寫書,試著記錄下她所推動的基層民主和自組織的故事,雖然寫書對人的影響力是緩慢的、不可計算的,但她謹記著每一個善意的迴響。在臺灣,寇姐更積極於溝通,她有寫專欄,在李明哲被捕後,她更是主動尋找傳遞資訊的機會,希望提醒臺灣人多多去了解中國。
「沒有人能選擇自己要出生在哪裡。」對於臺灣人與中國人之間經常產生的仇恨,寇姐說:「中國人也是,臺灣人也是。」
「對於臺灣人,很不幸地,你不得不了解中國。」寇姐說。「我能夠了解你們的感情。但如果說不理會中國,那就是把自己的命運交到別人手上。」對於臺灣與中國的未來,寇姐承認自己不是那個給答案的人,但她希望能拉動更多的臺灣人去看到這個問題、思考這個問題。
寇姐在臺灣的行動正如她曾為演講所下的標題所言:「我乾了,您隨意。」她並不強迫所有人都要聽她的理念,但她也沒有放棄溝通,選擇做那 0.001% 的行動者。
如芳草樸實而芬芳
結束訪問前,聊起寇姐的生活。寇姐的生活中充滿了植物,除了各種釀酒用的水果,她在被捕之前,曾經在老家思考過「自給自足」生活的可能性,自己種植各種植物。
問起她最喜歡的植物,寇姐先是思考了一下,然後回答說:「是有香味的草。」她輕鬆就列出了紫蘇、荊芥、薄荷和藿香,說在她家的院子種著許多,這些植物都有香氣,而且能夠食用。
而寇姐她本人似乎也正如芳草一般,沒有嬌艷的色彩與濃烈的香氣,但是卻安靜地、和緩地散發著淡淡香氣,願意為在生命旅途中遇到她的人,留下一絲的影響與改變。
「我不期待也不奢望改變這個世界,但這個世界也不會改變我。」寇姐這樣形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