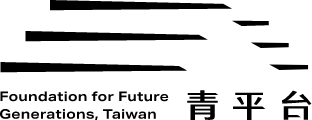為什麼在中國的體制下,還能養得出這樣子的「非典型中國人」?

 文:張瓊齡(台灣國際志工協會理事長)
文:張瓊齡(台灣國際志工協會理事長)
自1992年夏天,誤打誤撞進入台灣最大的NGO集團旗下擔任媒體記者以來,之後短暫在醫療學術基金會任職、在東部偏鄉戒毒中心擔任文宣企劃執行、參與花蓮社造及九二一災後花蓮社區防災專案人員、全台第一所社大行政部門主管、自由工作者與寫作者,二十多年的工作資歷都與NGO相關。
2000年台灣社會第一次政黨輪替,曾於2002~2003年短暫進入某中央部會擔任機要職,之後回到NGO擔任主管職近三年。此期間,眼見NGO為獲取穩定營運資源,積極爭取政府採購或委辦經費,在公辦民營的過程中逐漸被政府廠商化、體制化,除了日漸失去民間團體的自主性與創發力,同時也失去民間團體監督政府的超然立場。
由於對此種情境日漸感到不耐,亦有感於NGO從業人員長期以來或自我壓榨或在體制中集體相互壓榨的身心不健康之現象,並不值得繼續。基於不想爆肝死於辦公桌前,但仍願意留在NGO領域,於是決意找到適當時機離開組織,改以接案模式與NGO合作並互動至今。
2006年夏天,生平第二度踏上中國土地時,我已於年初離開最後一個專職的NGO職場,以freelancer身分在某國立大學NGO相關研究中心,負責執行當時的青輔會委託的國際志工專案。當時我隨著參訪團,以台灣國際志工協會副理事長的身分赴中國交流NGO實務經驗。相較於1992年在學生時代以藝文交流首度接觸中國,這次則以國際交流的角度看待彼此的互動,並意外種下往後十年(2006~2016年)主動與中國民間人事物接觸的契機。
然而,那年在檯面上交流過的單位組織或個人,後續我個人都沒有繼續接觸,倒是和一個我事前私下聯繫的公益旅遊組織結下不解之緣。後續因著這個組織的發起人,引介我鏈結上香港的社會企業推動人士,並於2010~2015年間,持續關注香港的社企發展。
回顧2006~2016年期間與中國民間人士的互動模式,大致有以下類型:
學術界與民間NGO聯合組團赴中國針對學術及實務交流。
以個人身分參與中國公益旅遊團體志願者活動。
前往中國踩點並接待中國大學環保社團學生領袖參訪交流台灣相關NGO。
透過移居中國的台灣舊識之經驗。
透過浩然基金會歷屆前往中國服務之台灣人員或外派中國人員。
安排及接待來台短期或較長期(四個月)主題參訪之人員或訪問學者。
與中國公益旅遊團體之人員共同前往第三國服務或體驗。
安排行程及陪同中國擬考察公辦民營模式之社福機構人員。
接待有意建立兩岸商業合作之考察者(直接或間接透過公益旅遊志工結識)。
與此前接觸過並後續發展出私人友誼者純粹結伴旅行。
透過前往中國長期工作的台灣國際志工友人。
伴隨出書機緣,與台灣國際志工友人由南到北,在中國幾所高校或NGO或私人場域分享國際服務主題。
2006~2012年期間,每年有一到數次前往中國,除了為兩岸交流的踩點行程曾獲委託單位來回機票補助,其他均為非公務性質的自費行程。
2013~2015年期間,由於對岸相熟的友人們及我本人在生涯選擇上,不約而同有所轉變,而我當時主要焦點聚焦在關注香港社企領域的發展,因此中斷主動前往中國的行程,而以香港社企界為主要參訪與交流目標。但仍被動接待來台短期參訪或居留數月的中國友人,以保持與中國方的接觸。
直到2016年下半年,職涯面臨調整有較長時間的空檔,又重啟睽違三年的中國。然而兩趟相隔約兩個月中國之行,讓我具體意識到中共官方對於NGO(尤其是與政府有購買關係的組織)的管控已經下達基層的最末稍。台灣NGO人士恐怕難以再用過去模式,隨意與對岸民間互動而不讓自己陷入險境,於是在十一月份的行程結束後,也同時決定暫緩前往中國。
 就在這個階段,經台灣NGO友人介紹中國作家K,因其有環島台灣、從異於過往的角度認識台灣之計畫;有鑑於我經常遊走台灣各地並廣泛接觸社造、社大、獨立書店或者小農、弱勢關懷、原住民議題,或可居中起引介作用。於是,我本人雖暫時中止前往中國,亦無主動關注中國議題之舉動。但由於參與過多次K在台灣各地的分享會與部分旅行台灣之行程,或者提供其暫時落腳處之機緣,2017年竟也透過這位流亡作家,接觸了一些中國相關議題與人士。
就在這個階段,經台灣NGO友人介紹中國作家K,因其有環島台灣、從異於過往的角度認識台灣之計畫;有鑑於我經常遊走台灣各地並廣泛接觸社造、社大、獨立書店或者小農、弱勢關懷、原住民議題,或可居中起引介作用。於是,我本人雖暫時中止前往中國,亦無主動關注中國議題之舉動。但由於參與過多次K在台灣各地的分享會與部分旅行台灣之行程,或者提供其暫時落腳處之機緣,2017年竟也透過這位流亡作家,接觸了一些中國相關議題與人士。
像我這樣一個並非外省後代,既無公務需求,亦沒有積極前進中國開展職涯規劃之人,何以在長達十、十一年的時間,自費前往中國或接待中國民間人士呢?
2006年那趟參訪,坦白說在北京、上海的官樣行程,並未引起我太多共鳴。是到了廣州由中山大學當時的公民社會中心安排的一場幾十個草根團體的大會師,會中那種奮發向上、革命之鄉的慷慨激昂,感染了我(返台後不久,就聽說該中心已經被抄了)。當時,我身在台灣NGO領域所感受到一種低迷氣息,已經好一段時日了,很好奇中國民間這些連立案都談不上的草根組織,打哪兒來的活潑生氣?
2009年初在北京,與一位透過浩然基金會計畫前往中國的台灣NGO資深同行交流。他說,中國正在經歷一個前所未有的時代,不想錯過,計畫告一段落後,即使自費,都願意留下來繼續觀察。
聞言,心有戚戚。
2006年某夏夜,在北京。
跟事先約好的某組織發起人在我下榻的酒店咖啡廳會面。當時適逢世足賽期間,會面後他得趕回去加班進行網路轉播相關工作。短短兩三小時,又是初次會面,我原本不預期會有多深刻的互動,然而,當我問起,以他的IT專業背景,何以年紀輕輕就投入關注偏鄉兒童的服務行動,他很自然地說,應該跟他的家庭背景相關,接著便簡單交代了自己的身世。
我萬分驚訝。
即使在台灣,再怎麼一見如故,也未必初見面就提自己身世,尤其是男性。
那天還發生一件糗事,我在台灣的工作一直忙到成行前一天深夜,一到北京跟他見面時身上沒有人民幣,我滿心以為下榻的酒店能刷信用卡,但其實不然,那天由他掏錢買單了我們兩人的消費後,便匆匆趕回去繼續加班。
這個人,在幾年後成為中國某類社會企業的代表人物,在港台也享有名聲,然而,我們見面那時際,他還從沒離開過中國國門,年紀約莫小我五歲左右。
跟他對話了一陣,我便忍不住問:「你,真的沒有離開過中國嗎?」
從他談吐中所顯露的大器與見識,我很難相信,這樣一個從小資賦優異、名校上來、該是躋身在主流社會拚搏的人,居然一路受中國的教育長大,卻又沒有長成那種台灣人印象中、很典型的中國人模樣。而他馬上要離開高薪工作、在最靠近人生的第一個一百萬(人民幣)財富的前夕,全力投入前途未卜的公益領域。
此後的十年裡,當我每遇見一個「非典型中國人」,我總是忍不住對他們個別感到好奇,然後自問:為什麼,在中國的體制下,還能養得出這樣子的人?
我當慶幸,在2006~2016年這段期間,是從NGO領域、社企領域,和個別的中國人有所交會與交集。哪怕一開始多少還是先接觸了組織,但往後就是直接和組織中較投合的個人有所互動,並持續彼此的情誼。
即使在台灣,我和朋友的互動基本上是「淡如水」狀態——就是一旦彼此認定是朋友,平日並不特別互動,但只要一相聚就是直接進入到深度模式。面對中國,我既不為了前進中國而準備,平生也沒有積極搞人際網絡的習慣,基本上跟中國友人就是比照淡如水模式,有一搭沒一搭地往來著。
由於台灣人前往中國向來容易,六年期的台胞證,只要事先加簽,後來可以落地加簽,一張機票或船票,甚至走香港陸路就過去了。到了2010年中國來台自由行開放後,部分友人們無須再經過繁複的邀請程序,也可以說來就來,而朋友交往久了,氣味相投,兩岸的界線無形中模糊掉了;2016年秋天,我甚至精心安排始終沒興趣到中國旅遊的母親,首次踏上中國土地。那回正巧朋友們都沒出遠門,既有旅行界、公益界、靈修界,堪稱是夢幻名單的友人、夢幻行程與接待。賓主盡歡,曾以為這會是另一個美好的開端。
這趟成行前夕,我使用多年的微信前所未有地不靈光,硬是斷訊幾天,直到我進入中國又恢復作業。但已不免讓我有所聯想,是否跟我在不久前結識了流亡來台的作家K、而我在當天透過微信發私訊,告訴兩位中國友人此事有關?
對岸兩位友人對我的訊息完全沒回應,原以為是內容敏感不方便回,後來才得知,恐怕該訊息被屏蔽,朋友根本沒有收到。基於某種敏感,我事先交代同行友人,萬一過海關時我有狀況,請務必照顧我媽媽,莫讓她受到太多驚嚇。雖然這事沒真的發生在我身上,但是五個月後,李明哲在入境中國過程中發生了。
我在2016年最後一趟的廈門行,得知所有與政府有購買關係的NGO都必須成立共產黨支部,而當地的社區大學也都結合黨資源辦理並對共產黨員採取優惠,這些已足以讓我感知,兩岸之間NGO在這樣的氛圍中,再無可能一如過往自在互動無所顧慮。當下我已沒有意願冒險繼續協助公益領域的友人引進台灣經驗;李明哲事件發生後,我更加相信,長久在習於無所忌憚發言與自由行動的台灣人,極可能因為對議題性質與發言尺度拿捏失去警覺,在不自覺中讓自己陷入險境。
 突然間,莫名的恐懼蔓延開來,無邊無際,壓過了我持續十年的好奇心。
突然間,莫名的恐懼蔓延開來,無邊無際,壓過了我持續十年的好奇心。
其實,真正有具體恐懼經驗的人,是那些被中國政府抓捕關押過倖存、乃至於被迫必須流亡的人。他們應該更加戒慎恐懼,並且在恐懼中噤聲並失去行動力。
但事實上,卻又不是這樣。
透過流亡來台的K,透過她在台灣各處環島分享,讓我發現還有許多焚而不毀的生命,繼續頑強地堅持住原本的信念,不因打壓抓捕監禁而有所改變。尤其這些人都已是中壯年,並不是血氣方剛、一無所有、充滿浪漫思維的年輕人。他們不是不明白堅持所需要付出的代價,不是不知道堅持了以後仍有可能一事無成。
我原以為自己的莫名恐懼還會再持續得更久一點,原以為恐懼後遺症應該沒那麼容易可以擺脫的K,在環島的時候需要更多的陪伴才會有足夠的安全感。
但我完全想錯。
當我們提出希望組織環島陪走團,讓K不要有落單的時候,K卻拒絕被恐懼思維綁架。她面對恐懼的方式是正面迎擊,而不是龜縮退避,試圖尋求更多的保護。在為期將近一年、點狀的接觸與相處後,我發現對於恐懼無畏的K用她的安定引渡了我,不繼續被無端的恐懼所駭。
2017這一年,我沒到中國,卻透過流亡來台的人,繼續認識中國的奇葩們。
一如過往,我依然止不住地好奇,問天:
為什麼,在中國的體制下,能養得出這樣子的人來?
為什麼,在中國的壓制下,毀滅不了這樣子的人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