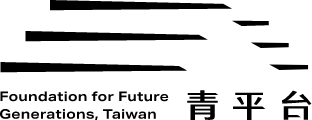六四屠殺與二二八的對談:沒有加害者,怎麼談轉型正義?

 文:李奕萱
文:李奕萱
這篇文章是摘錄和改寫自青平台與李明哲救援大隊、哲學星期五、華人民主書院於4月19日所共同舉辦的【明哲之夜 (2) 如何面對政治屠殺和傷痕:中國六四和台灣二二八】。這是一場跨國界、跨世代,兩位與談人均出身歷史研究專業,又兼具政治實踐經驗,將從中國六四和台灣二二八的對照出發,展開一場關於國家暴力與轉型正義的深度對話。
與談人簡介
吳仁華
八九民運的參與者和見證人,歷史文獻學者。六四後流亡海外,長期參與中國海外民主運動,曾任《新聞自由導報》總編輯,中國憲政協進會秘書長。1989年以政法大學教師身分參與天安門民主運動,是首次遊行的組織者之一,曾任新華門絕食請願區負責人,在天安門廣場親身經歷清場過程。1990年2月從珠海跳海偷渡香港,輾轉定居美國。著有《六四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六四屠殺內幕解密: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等書,均由台灣允晨出版社印行。
嚴婉玲
野草莓學運、反黑箱服貿運動參與者,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主要研究範疇是日治至戰後的台灣政治史、文化史。學術之外對於社會議題也高度關心,曾參與發起成立社會民主黨並擔任秘書長,目前在台南與一群青年成立「台南新芽協會」,期待在故鄉打開更多公共討論與行動的空間。
近年轉型正義的呼聲逐漸升溫,在以轉型正義作為關鍵政策的蔡英文總統上任後,去(2017)年底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今(2018)年5月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正式掛牌成立,相關論戰更是在今年達到一個沸點。短短半年內,與其相關的爭議接連爆發:向蔣中正陵寢及銅像潑漆、國民黨新北市市長候選人侯友宜也被人起底曾是拘捕鄭南榕的刑警,再再引發大眾對轉型正義的討論。
提到台灣轉型正義,經常會有兩極的評價,有人認為轉型正義淪為「政黨鬥爭」,也覺得社會應該要「向前看」了。然而在這樣聲音的另一頭,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意見,批評台灣的轉型正義大有不足,威權遺緒依然深植生活。
描寫二二八事件的畫作「恐怖的檢查」
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六四屠殺見證人吳仁華參觀二二八紀念館後,感想是「非常不滿意」,直言二二八事件受難者的紀錄不足,更是缺少加害者的資訊:
二二八死傷那麼多人,難道都是台灣前行政長官陳儀殺的嗎?難道都是警總殺的嗎?天安門事件也是這樣,數以千計的北京學生、市民死亡,破萬人受傷,難道都是鄧小平殺的?這麼重大的人權災難事件,不能只有一個主要責任者。
台灣曾做過二二八平反運動研究的嚴婉玲也指出,台灣普遍存在「只需要追究官員、底下奉命行事的人員不必追究」的想法,當她參與「戒嚴時期不當審判補償基金會」的資料庫建檔會議時,軍方的人堅持不公開不當審判案件的軍法官姓名。類似的事件層出不窮,時過已久的事件、社會的氛圍與官方的態度下,台灣轉型正義磕磕絆絆的路途上,查到加害者的身份難,讓其公開更難。
互聯網埋伏只為找到殺人坦克兇手
二二八事件發生於1947年,時間的沖刷再加上國民政府統治下的長期噤聲,尋找加害者與受害者的路並不容易;六四屠殺發生時間較晚,然而追尋真相的難度在中國的層層封鎖下,恐怕不亞於二二八事件。
吳仁華1989年任教於中國政法大學,與學生一起參與八九民運,堅守天安門廣場,直到最後才撤離。吳仁華依然記得當初的恐懼:
那是我有生以來經歷過最可怕的事情,天空上都是子彈畫出來的彈道,兩邊都是裝甲車、戴鋼盔的軍人。
六四屠殺後,他逃離中國,定居美國。六四屠殺宛如他人生的分水嶺,有感於事件真相的缺失,他全心投入六四屠殺及事件後的鎮壓、清理的研究,透過網路上零碎的資料與線索,抽絲剝繭拼湊出部分的真相,建立加害者與受害者名單,被視為研究六四天安門事件的第一人。
吳仁華的方法相當土法煉鋼,以自己擔任新聞工作者的經驗及學校考據學、目錄學的知識為本,在網路上大海撈針,利用不同的關鍵字搜尋資料,輔以中國政府宣傳平息反抗的書籍,一一比對、鑑定軍人姓名與部隊番號。「像小孩拼拼圖一樣,把真相拼出來。」吳仁華如此比喻。
接著,他把目標轉到互聯網上的退伍軍人、轉業軍人,雖然這些人對工作都有保密的義務,但在聊天時還是可能不小心暴露出部隊的番號。「我甚至進入各軍團的聊天室,每天都跟他們聊天。」吳仁華笑道。最後,他追出了血洗天安門的部隊名單,更是解開他多年來最耿耿於懷的問題:那輛追壓學生隊伍、造成11名學生死亡的坦克車上有誰?
二二八遲到太久的真相追查
相比於六四屠殺在中國依然是「不能說的秘密」,目前台灣已可以對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暢所欲言,然而「缺乏加害者資訊」這點卻和六四屠殺有類似的困境。嚴婉玲說:
二二八事件的加害者的確不好找,但吳老師都可以找到四、五零年代國共抗戰部隊的番號了,憑什麼二二八找不到呢?
她也更進一步提出:
找到跟被列出來、被看到又是另外一回事,我們可能會看到柯遠芬、彭孟緝、陳儀,再下來就沒了。但如果仔細看二二八研究的專著,還是會找到一些軍官的人名,只是這些不會被放到紀念館去。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二二八真相追查遲到太久了,長時間的言論控制延滯了應有的真相調查,白色恐怖的氛圍宛如濃霧包圍了民間。嚴婉玲舉例,1950年代,她父親的高職同學參加壁報比賽,畫了一個運動會上的跑者,好死不死,跑者的臂章號碼正是「228」,兩天後,這位同學就被請去約談。
在充斥恐懼的氛圍中,一個突破口在於海外的民主運動人士,許多逃出了台灣的菁英持續紀念二二八事件,日本的台灣青年社從1970年代開始,每年舉辦二二八紀念會,讓大家發表對二二八事件的個人感知。可惜這些紀念對真相的追蹤幫助有限,所得到的資料大多是斷簡殘編。
至於國內開始普遍談論二二八事件時,已經到了二二八事件40週年的1987年。當時,鄭南榕促成了二二八平反運動,串連各縣市發起民間自主遊行,才讓二二八事件見了光。隨著解嚴的鬆綁,二二八公義和平運動開始遍地開花,學術研究也加入了真相揭露的行列。然而時過四十年,很多受難者都已經過世,也有些仍在世的當事人不願意重提事件,一開始連做口述歷史、文獻資料的搜集都頗為艱辛。
轉型正義三步驟:還原真相、追究責任、社會和解
隨著對真相要求的呼聲上漲,二二八比較完整的報告陸續出爐,1989年在嘉義建立了第一座二二八紀念碑,1996年李登輝前總統為二二八事件公開道歉。乍看之下,二二八逐漸被平反,真相逐漸浮出水面,然而事實上,台灣的轉型正義始終有所缺陷。
吳仁華說明轉型正義應有的步驟有三:第一,還原真相。第二,追究責任。吳仁華認為,加害者都要被紀錄,就算只是聽命行事也不得豁免,就像東德射殺翻越柏林圍牆的士兵也需要受到審判一樣。「前面兩個步驟都做到後,第三步才是社會和解。」吳仁華說:「台灣第二點沒有做到的話,不是二二八事件平反了、建立紀念碑了、有紀念館了、給賠償金了,就算是轉型正義。」
實際上該如何執行,嚴婉玲則提到各國不同的作法:西班牙對獨裁「刻意失憶」三十年後,通過《歷史記憶法》,並在今年決議將已故獨裁者佛朗哥遷出「烈士谷」;南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致力於還原真相,卻缺乏追究與懲罰;南韓光州事件針對執政首謀者進行懲罰,對運動過程中的死者家屬進行補償與名譽平反。每個國家的做法不盡相同,嚴婉玲也承認,轉型正義不是一個中性的名詞,政治的角力勢必伴隨其中——台灣也是如此。
台灣沒有暴力鬥爭、緩慢進入民主化的特殊歷程,讓轉型正義卡在一個特殊的困境中,雖然在各方力量的拉鋸下,台灣目前轉型正義已經有了一定成果,然而與零分進步到六十分相比,從六十分走到一百分的路途必定更為險峻。未來轉型正義的應如何走下去,嚴婉玲認為,最重要的不是當權者怎麼想,而是取決於台灣人民對轉型正義的想像是什麼。
真相揭露、傳達依然需努力
學者對於真相的執著,讓原本深埋的真相有機會看見天光。儘管吳仁華對中國言論控管感到無奈,他依然堅持自己的信念,著手製作六四受難者的名錄。吳仁華說:
我個人能力有限,但我有心要做,再艱難也會做。這麼重大的國家人權災難事件,做這樣的紀錄是最基本的。
而對於從研究者變成執行者的嚴婉玲來說,在台灣已經有許多調查與研究的情況下,下一步最重要的是讓真相被更多人看到。
網路是搜集資料、傳遞資訊非常重要的工具,可是網路也是限縮言論的工具。
嚴婉玲擔心如果民眾都安於自己的同溫層,即使史實、真相陸續揭露,也難以觸及更多的群眾。因此如何傳達正確的資訊給更多的人,將是未來的課題。 儘管面對的問題有所不同,台灣及中國在追求真相、轉型正義的過程依然有其類似之處,值得彼此借鏡。雖然前路漫漫,但現在能做到的,就是不要讓真相沈睡在歷史的角落,至於未來將要何去何從,就得回歸到各自人民對社會的想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