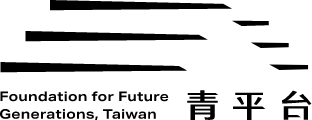轉型正義怎麼做?從德國經驗回看台灣民間行動(上)

 文/ 李奕萱 照片來源:Jeanne Menjoulet
文/ 李奕萱 照片來源:Jeanne Menjoulet
2019年4月29日,南投東埔部落族人Bukun(伍金山)來到臺北,在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後簡稱促轉會)的陪同下,在六張犁見到未曾謀面父親的墓。1952年,Bukun時任警察的父親伍保忠被懷疑參與叛亂組織,遭到逮補,在羈押期間因病死亡。
遲遲沒送到的死亡通知,讓家人從來不知道他的下落,直到促轉會帶著判決書、死亡證明等檔案拜訪,等待超過六十年的真相才終於到來。伍保忠的故事並不是個案,直到現在,也還有受難者家屬等不到答案。
大約從2000年後,開始有「轉型正義」的訴求聲音,民間開始自主運作,搜集口述歷史,還原真相,蔡英文上任總統後,政府也開始推動轉型正義,2018年促轉會的成立,是一大里程碑。然而,往前進的同時,也會有反作用力,轉型正義被放上檯面後,反對的聲音不斷湧出,「追殺」、「鬥爭」的質疑不停,也有人再三強調:「歷史已經過去了,該往前看了」。
只看到眼前問題時,視野會變狹窄,這時或許可以退一步,看看已經推行轉型正義許久的德國怎麼做。德國轉型正義主要可以分兩塊談,一部份是如何面對納粹屠殺,另一部份則與臺灣較類似,是東德共產政府對人民的高壓統治。
先有真相,再來談和解
那是個與白色恐怖有很高既視感的年代。東德情治機構裡,被記錄在案的人數高達五百萬人,是當時人口三分之一,而替國家安全局工作的更多達二十七萬人。在東德生活可謂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一個不小心,就有可能失去學籍、工作、甚至被關進大牢。
現在,這些檔案均存放在前東德國家安全部檔案局(BStU),德國用政府的錢、追討的黨產成立基金會,開始做檔案的解密。
檔案局裡檔案如山,解密也非同小可,很多都不是用德文寫,而是以數學符號、代號、拉丁文拼寫,只有當初的負責人才懂其中玄機。因此,基金會現階段最大的工作就是翻譯檔案。
投入這麼多為了什麼?長期參與轉型正義議題、目前於德國攻讀博士的鄭嘉瑩說:「檔案局的答案很簡單:『因為要給受難者一個真相。』」
鄭嘉瑩舉例,現任德國總理梅克爾出身東德,她曾在觀看一個民主示威活動後,被學校開除。疑問放在心頭多年,直到當了總理,有作家訪調她的人生,才知道是室友打小報告,說她去參與抗議活動。
「臺灣曾經也是這樣,莫名其妙就進了監獄、被槍決。臺灣還有很多這樣的檔案沒有被公開、不見了,久了,大家就會忘記了。」鄭嘉瑩說。
德國在合併之初,對於檔案是否應該公開,曾經過激烈討論。政治領袖擔心檔案曝光會造成社會動盪,然而,當東德的民運領袖幾次發現身旁夥伴是線民,他們開始訴求保留檔案,並開放調閱。經過幾次衝突,終於訂立〈史塔西檔案法(Stasi-Unterlagen Gesetz)〉,明確規範檔案用途、調閱方式。
鄭嘉瑩提到,現在,每個當事人都可以免費申請自己的相關檔案,從開始解密到交付檔案,中間要花上兩年半的時間——儘管耗時費力,德國還是將真相還原放在第一順位。
找出加害者不是為了報復
鄭嘉瑩認為,歐洲的轉型正義經驗中,最值得警惕與學習的,是找出加害者:「事情有因才有果,莫名成為受害者一定有原因。找出加害者不是為了報復,在歐洲,除了特定的人有受到法律上的審判,大多數都是無罪的。加害者往往是受難者身邊重要的人:朋友、親人、或是同事,他們可能迫於某些因素才這樣做。」
德國不只執著於找出加害者,也認真處理東德政權遺留下的問題。號稱歐洲最有錢政黨「前東德社會主義統一黨(SED)」的黨產遭清查、追回,部分用於推動轉型正義的基金會,剩下則回饋到東德人民手中,作為青年就業、交通、文化及歷史工作的經費。東德政黨曾經的聚會所、黨部改為現在的教育會館,展示當地發生過的不義事件,並定期更新展覽。
從德國經驗出發,鄭嘉瑩希望大家回頭看向臺灣,婦聯會385億的不當取得財產是否能收回、收回後要做什麼,目前都還是未知數。在空間的轉型上,中正紀念堂將何去何從,仍備受爭論,還有許多不義遺址甚至還沒開始處理,例如曾經是特務機關的警備總部,沒有經過徹查,就繼續為政府機關沿用。
德國不只針對黨產做處理,針對前共產黨公務員,德國也訂定〈除垢法〉,全數開除,經過調查後沒有重大罪行紀錄,才能回聘。影響體制內工作者的做法在德國遇到不少反彈,然而鄭嘉瑩依然希望,這樣的經驗能讓臺灣更深入考量,而非迴避問題:「我們選擇什麼都不談,很少人做相關的研究,很少人談除垢,但不碰加害者議題真的是好的嗎?」
從教育落實轉型正義
同樣對轉型正義議題抱持興趣,政大東亞所研究生陳宥喬選了和鄭嘉瑩不一樣的切入點,趁交換期間,研究了德國教育如何談論納粹統治。
陳宥喬指出,德國歷史教學法有明定兩大原則:第一個是1960年代發展出的「歷史意識」,要讓學生意識到人類的存在、制度、文化都有歷史性,了解生活面向包含過去、現在、未來;第二個則是1970年代發展出的「歷史文化」,強調歷史的多元性,讓學生注意周遭環境,透過不同媒介了解歷史,進而形成個人觀點。
1976年,Beutelsbach小鎮的政治教育會議中,訂定德國公民教育準則,成為後來備受參照的教學依據:歷史必須要「被有爭議地教」,歷史事件具有多面性,老師的任務是呈現多元性,讓學生學習思考與判斷,結論是什麼並不那麼重要,重點是思辨的過程。
任教於布來梅邦一所中學的老師瓦爾特克(Elisabeth Waltke)在課堂上有三階段:給學生一份原始文件、讓學生解釋與分析、最後給予評價。有時,她也會帶學生走出教室,來一堂「室外歷史課」,透過參觀展覽來與學生對話,形塑對歷史的認識。
在德國,實際的體驗的課程相當常見。陳宥喬報名集中營一日導覽時,就聽到導遊說,自己的女兒將要到婦女集中營過夜。陳宥喬的德國朋友也向她分享,學校曾經安排倖存者到班上做經歷分享,印象格外深刻。
回到制度內的課綱,德國現在的歷史課本從1950年代偏重戰爭輸贏的論述,經過1963年追究集中營人員責任的法蘭克福審判、1968年反權威統治的六八學運,才演變成現在「民主與獨裁」的論述框架。陳宥喬特別點出,德國課綱採取柔性課綱,只會規範基本原則及必須論及的要素,不像臺灣的硬性課綱,會逐一列出小的歷史事件。
用整個城市來記憶歷史
在柏林,針對納粹時期有三百多處不同的紀念遺址、學術機構和博物館。陳宥喬採訪恐怖政治地形館(Topographie des Terrors)發言人,了解他們如何透過展覽做歷史教育。
1987年,現任恐怖政治地形館基金會執行長哈瑪(Andreas Nachama)在「蓋世太保」總營原址舉辦露天展覽,講述納粹在該處犯下的恐怖行為,獲得良好迴響。1992年,在柏林市政府的支持下,展覽擴充為公民獨立基金會。2010年恐怖政治地形館正式開幕,從加害者的角度切入介紹歷史。館內常設展分析納粹1933年到二戰結束的政策、組織、大規模的屠殺行為以及對受害族群產生的影響,在館外的柏林圍牆上,則展示納粹的宣傳手法。
恐怖政治地形館定期會舉辦給學生的工作坊,向學生介紹納粹組織中各領導者的名字、職務,特別的是,他們會把所有名字都點出,因為他們希望讓學生知道,納粹是由很多「個人」集結起來的「系統」。
除了恐怖政治地形館,柏林也有猶太人博物館,展示猶太人相關的歷史與二戰的受難,其中最有名的便是以色列藝術家的作品,將一萬多個鐵製的臉放在地上,參訪的人踩在其上時,發出的金屬碰撞聲就像是受害者的吶喊。在蒂爾公園(Tiergarten)裡,則有同性戀受難者紀念碑,提醒民眾,納粹影響的受難者不只猶太人,還有非猶太裔的波蘭人、精神病患以及同性戀,
教育並不只是老師和博物館的工作,政府也是其中重要一環,總部位於波昂的聯邦公民教育中心是德國歷史教育的重要推手,他們針對不同年齡層做免費出版品、架設介紹柏林圍牆的網站、舉辦以色列城市導覽,希望藉此形塑民主價值,並培養公民思辨能力。
陳宥喬印象很深刻的是,許多受訪者都強調,做這麼多,就是為了記取歷史教訓,不讓歷史重演,德國聯邦總統史丹麥爾( Steinmeier)亦曾說:「誠實的記憶,是今日我們身份認同的基石。」
什麼是轉型正義?
從找尋真相開始,到試圖處理威權政府的遺緒,進而培養公民對議題的思考,轉型正義從來不是一蹴可及。德國在戰後到1980年以前,也曾經有一段時間,大家都說:「過了就過了,不要再談了」、「要放下過去,走向未來」。而甚至到最近,依然會有人隱晦地推崇大力追求經濟發展,號稱不談政治的希特勒。無論是在哪個國家,轉型正義都是一場彷彿永遠走不完的長征。
所以轉型正義到底是什麼呢?鄭嘉瑩提到,轉型正義(transitional justice)翻譯自英語,在德國並沒有這樣的說法,德國人用的詞是克服過去(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與清理過去(Geschichtsaufarbeitung),前者主要說的是如何站在傷痕上往前看,後者則是強調對過去的處理。鄭嘉瑩由此做了一個小的結論:「無論說法是什麼,講的都是同一件事:要有過去,才會有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