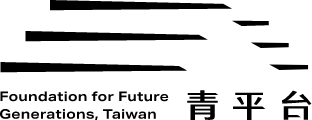轉型正義怎麼做?從德國經驗回看臺灣民間行動(下)

 文/李奕萱 照片來源:ølivier
文/李奕萱 照片來源:ølivier
對於納粹、共產黨的歷史傷痕,德國從檔案、空間、除垢、教育等方向下手,政府、民間相互配合,共同推動轉型正義。回到臺灣,轉型正義最早是由民間力量開始,從下而上地推動,才能走到現在的成果。直到現在,依然有許多不同身份、領域的人,用自己的方式來替轉型正義進一份心力。
創辦共生音樂節,用年輕人的語言來說歷史
共生音樂節創辦人藍士博笑說:「關於轉型正義或是對臺灣歷史的理解,我跟年輕人可能已經是不同世代。我剛聽到時,就像是被雷打到的感覺,開始發現世界跟想像的不太相同。」因為這樣的「天啓」,他開始思考自己能發揮什麼樣的力量,讓議題被更多人看到。
藍士博替史明做口述歷史時,受邀參與長輩在自由廣場舉辦的二二八紀念活動。當他抵達現場,卻發現活動臺下都是六、七十歲的長輩,人數也只有一、兩百。三個多月後,他在同個場地參與六四事件紀念晚會,現場的熱絡讓他大吃一驚。他因此醒悟:「歷史之於我們的意義是一樣重要的,但是能不能被接受、能不能吸引到別人,是方法的問題。」
因此,藍士博創辦了共生音樂節,透過音樂會吸引年輕人參與,並製作自己的產品、與非營利組織合作,創造曝光機會,最後再透過現場的二二八事件展覽、感性與知性的短講,讓更多人認識二二八事件。
為了讓活動保持創新力,他們年年更新團隊,因而催生了許多有趣的想法:他們曾經透過街頭快閃宣傳共生音樂節,也曾經在學測社會科考試前,發放有關臺灣歷史、二二八事件的題目;還有一次,他們在萬華區、中正區的中國時報、聯合報中放入夾報,內容正是關於二二八事件與共生音樂節。
不過無論有多少花招,最核心的始終是靜態展覽的內容,團隊會花整整半年的時間閱讀、討論、書寫。
「可能會有人問,為什麼要辦共生音樂節?簡單來說,我們想要選擇年輕人喜歡的方式。」藍士博認為:「歷史事件如果沒辦法被感受、被閱讀、被理解、被銘刻在心裡的話,就像是不存在一樣。」
從埋首檔案到走入社會,試圖形塑集體記憶
共生音樂節舉辦多年後,為了更穩定、組織化地運作,便創立「臺灣共生青年協會」,理事長是李思儀,她曾參與主辦第五屆共生音樂節,而在更之前,她就讀於臺大歷史學研究所,參與編纂中研院臺史所《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史料彙編》,論文主題是〈二二八事件期間雲嘉南地區青年學生的反抗行動〉。
長年泡在檔案裡,李思儀有許多心得:「我們想到檔案,可能會覺得一直存在官方的檔案庫,但其實沒有,很多沒有受到公務員重視,就沒有交出來;或是在轉型的過程中,一些檔案就繼續存放在過去的機關裡面。」
會有《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史料彙編》系列書籍,也是起源自2008臺史所研究員在二手書商拿到的一系列檔案,內容廣及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的情治監控。原來,一位工作於保密局臺灣站的情治人員退休後,把資料帶回家,因緣際會下,後代就把檔案轉手給二手書商,檔案最終才得以重見天日。
「這批檔案裡面有很多各縣市的自新名冊,可以看出,二二八事件的影響比大家想像中大。」李思儀提到,從檔案中他們也得知,儘管被害者賠償工作已進行多年,但仍有可能的受害者存在。
在參與研究工作多年後,李思儀決定走入社會,試著把故事告訴更多人。法國記憶研究《記憶所繫之處》提到,歷史研究來自個人記憶,個人記憶由歷史學者去彙整,看到更全面的狀況,最後形成集體記憶。李思儀認為:「二二八事件的研究有很多來自各人的口述歷史,研究也建立了,但集體記憶還沒有形成,這也是為什麼我參與共生音樂節,希望把學術的成果透過音樂節的方式,傳遞給青年朋友和社會大眾。」
用舞蹈傳承歷史,訴說曾經不能說的故事
同樣用藝術說歷史,蔡瑞月舞蹈節也是每年備受關注的活動。蔡瑞月舞蹈社編舞家詹天甄多次參與蔡瑞月舞蹈節,試著向大眾訴說歷史的傷痛。
詹天甄成長於戒嚴時期,她印象最深刻的事件,就是鄭南榕自焚後的出殯。那天她坐車經過士林,馬路上滿是黑衣人,開始有很多人抱怨塞車、咒罵街上的人,當時的詹天甄什麼都不知道,只知道報紙寫說鄭南榕是個暴徒。事後回想起來,她覺得非常受傷,就像她開始聽聞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受難家屬的故事一樣痛苦,覺得被深信的世界背叛,。
詹天甄曾就讀標榜為全國舞蹈最高學府的國立藝術學院,學校課程中沒有臺灣舞蹈史,她曾因此以為臺灣文化水平落後。直到她遇見啟蒙老師蔡瑞月,她才意識到臺灣早有如此厲害的舞者,當她得知蔡瑞月在白色恐怖時期的遭遇,更是讓大受衝擊。
蔡瑞月出生於日治時期,高中畢業後留日學習現代舞,曾在南洋有600多場的舞台經驗,回臺後,也曾在臺北中山堂表演。然而,她的丈夫因「通匪」之罪被驅逐出境,她也受牽連入獄,監禁於綠島3年。出獄後噩夢未完,她每天要向政府回報狀況,政府隨時一則通知,就可命令她到指定地點表演。
「蔡老師出獄後,跟國際音樂家馬思聰合作,編創〈晚霞〉,花了七年的時間,都已經講好內容,結果文工會(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文化傳播工作會)卻跟老師說,要找國立一專的師生來幫忙,慢慢地,就把演出蠶食鯨吞,最後還把作品拿去慶祝中華民國70年國慶,在報紙上發布:蔡瑞月跟他兒子退出演出!」詹天甄語氣猶帶憤恨不平。
看著老師受苦,聽著受難者的悲傷,她因此開始投入轉型正義,以舞蹈做為介入社會的工具。1994年,蔡瑞月舞蹈研究社面臨強拆,她自願與夥伴爬上吊車,高吊15層樓長達24小時,宣示反迫遷的決心。而現在每一次的蔡瑞月舞蹈節,也總會看到詹天甄的身影,或編舞、或表演,她總不會缺席。
哼哼唱唱,譜出白色恐怖的記憶
參與轉型正義的行動可以是大規模的活動,但也可以小至個人。臺北大學法律系四年級的李承哲於去(2018)年與夥伴們完成了一張專輯《上溫暖的勇氣》,用不一樣的方式來談論轉型正義。
故事的開始要先拉回他的大二,李承哲參加了國家人權博物館人權營,第一次接觸轉型正義,他震驚於國家對基本權利的侵犯,滿腔熱血想為議題貢獻一己之力。
經過了兩年的沈澱,他開始思考,能否用比較溫和的方式,來傳遞自己相信的理念。於是,沒有音樂底子的他,在擔任去年人權營的工作人員之後,與營隊的夥伴一同譜曲寫歌,並把歌曲整理成專輯,希望透過音樂轉述自己對受難者故事的想法,讓更多人有所共鳴。
李承哲與朋友的自創曲是《向陽的百合花》,不懂樂理的兩人在腦中模擬旋律,透過哼唱的方式錄音,再找人幫忙寫成譜。為了讓音樂不那麼單薄,他們特地找了音樂創作者艾文幫忙編曲、錄製。最後的專輯包含三首學員自創曲,以及一首合唱曲《千風之歌》,《千風之歌》原為政治受難者用來紀念獄中去世好友的歌曲,透過這次機會,他們以二十人的合唱重新演繹。
李承哲表示:「當我們講『正義』的時候,好像就會立刻阻斷對話的可能,因為像是在說,不同立場的人是不正義的。轉型正義需要更多的說明與討論,所以我才透過音樂、故事,希望讓更多人認識這段歷史。」
不過,他也承認,雖然一群人做專輯做得開心,但效應很有限,並不容易喚起社會大眾的重視。即便如此,他還是認為這是一種自我培力:「想要傳遞的理念即便微不足道,只要相信那是正確的,就可以用你最擅長熟悉的方式,找一群認同你的夥伴,完成這樣的一件事。雖然不是特別厲害,但只要對自己的人生厲害就夠了!」
從參加營隊到畢業論文自主研究
同樣是學生的,還有東吳大學政治系四年級的孟嘉美,她的畢業論文以轉型正義為題,研究讓讓府願意在民主化三十年後,推動轉型正義的因素。
她的轉型正義啟蒙,來自現任國家人權博物館館長陳俊宏。在學校修完陳俊宏的一門課後,陳俊宏推薦她參加綠島人權營。填寫報名表時,她翻閱了學術文章、網路資料,因而接觸到轉型正義。當她實際踏上綠島,看到關押的現場,聽受難者講述故事,更是感到震撼萬分。
離開綠島,孟嘉美選擇繼續認識轉型正義,她先是修習「死刑與人權」,研究特別刑法與白色恐怖的關聯,後來又在畢業前夕,開始做受難者視角的轉型正義研究。
學者艾斯特(Jon Elster)曾指出:「民主化時刻越遠,轉型正義被實踐的可能也會隨之降低。」孟嘉美針對這個論點深入研究,在吳乃德、吳叡人的論文中找到原因:第一,道德難題會開始出現,民主化剛開始,民眾會想把過去的不平等去除,因此道德要求會比較低;再者,民眾的遺忘加上許多社會的困境,也會導致轉型正義無法實現。
既然困難重重,是什麼讓政府願意在民主化三十年後,啟動轉型正義呢?孟嘉美試圖尋找答案,訪調三個主要的政治受難者組織:臺灣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臺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五十年代白色恐怖案件平反促進會。過程中,她注意到受難者組織的出現,很多是因為出獄後,被警察針對、被監聽、無法找工作,為了生活,才慢慢集結。她也看見受難者組織不同的統獨立場及意識形態光譜,開始可以用更全觀的視角來分析。
研究的最後,她很希望能找出轉型正義超脫政治任期的解方,她論文中特別提到,西班牙的轉型正義因保守派上任,歷史記憶項目就被刪減了70%運作基金。而她的設想是,從婦聯會回收的錢,是否能透過公共討論或制定相關法律,用於延續轉型正義。
轉型正義的未竟之業
從缺乏轉型正義的民主化,到民間自主聚集互助,追求真相,最後才得以由上而下,以政府的角色來進行。轉型正義走到今天,依然有不少課題需要處理。
藍士博提到,轉型正義要如何深入民間社會,仍是最大考驗。教育是一大困境,不只是師資、課綱、教材的問題,考試制度也限制了學生選擇題以外的思考;此外,在有了人權館、二二八紀念館、不當遺址之後,下一步要思考的,就是用什麼樣的框架跟結構,才能把目前的資源做整理及盤點,讓不同領域的人都能得到資源。
而轉型正義對臺灣究竟有什麼樣的意義?李思儀認為,轉型正義是一個過程,最終目標是追尋臺灣社會所需要的正義。李思儀說:「正義到底是什麼?我們還不知道,但臺灣的經驗會得出我們想要的是什麼。」
孟嘉美呼應李思儀的說法,認為轉型正義的「正義」沒有公認的定義,只能透過個人生命經驗,與社會議題對話,不斷自我辯證,才得以產生。不過她提醒,社群共識中的正義,跟政治受難者的正義可能就會有所差異,要怎麼尊重受難者的想法,而不是強加大眾的想像,將是未來的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