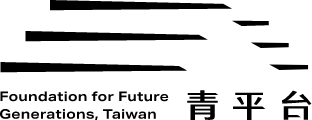愛琳娜,關於魯蛇救贖的寓言

真的很悶。
想想去年、前年,台灣社會風起雲湧的抗議,軍中人權、反服貿協議、核四停建,台北街頭動輒數十萬人劇中抗議,不管自己是站在群眾的哪一邊,這兩年,任誰都不得不承認:過去這兩年,真的是驚心動魄、目不暇給的兩年。
但今年到現在呢?只看到工作一樣難找、房價仍然上漲、薪水仍然低迷、食物仍然不安全、媒體上的名嘴照常喇賽,政府沒解決任何事,卻把大家弄的更煩躁。不是說我們想要無風起浪,沒事找事惹是生非,而是:明明感覺到台灣社會裡潛藏著巨大不安,隱隱騷動,但表面上卻風平浪靜,好像沒事似的。一股煩悶,在周遭蔓延。
就是那種夏日午後,烏雲密布,就是不下雨,濕熱地叫人難受,悶!
更像擠不出膿的青春痘,都已經作痛了,但不冒出頭,就看不到解決的那天。你不願跟膿包「和解」,它卻黏在你身上,吸你的血,逼你跟它「共生」,悶!
這是一種想快速了斷,但卻沒辦法了斷的感覺;是一種自己頑強地不服氣,環境卻逼你要放棄的感覺。
這種被環境壓趴在地上的感覺,有沒有人可以體會啊?有沒有哪首歌,可以唱出你我的心情?哪本小說,可以寫出你我的故事?那部電影可以講出來我們魯蛇的心聲,掏掏生活的鬱卒……幫幫忙吧!
〈愛琳娜〉,林靖傑的電影。

女主角,高雄女工陳愛琳,在一次車禍中把握賠償的機會,順利轉型成小提琴老師,卻沒想到這並沒有使她翻身成為小資女,而仍必須四處賣藝,一樣勞碌。於是,陳愛琳勇於相親,閱人無數,就是希望能找到好桃花,把自己嫁掉,翻身過好生活。但幸運並沒說來就來,先是曾以為是真命天子的小開,在得知陳愛琳意外懷孕後避不見面;再來是父親病重入院、兄長事業徹底倒閉,整個困局逼使女主角徹底覺悟:不能再這樣等別人、不能再這樣廢下去!她想起了童年時一場逆轉勝的經驗,變身為蒙面女俠,以小提琴的琴聲,振奮蒼白的通勤族、聲援失業的關廠工人、挺身對抗都更財團、守護自己的家園。
陳愛琳的決意,鼓舞了社會大眾也鼓舞了自己。她終於發現,期待已久的幸福就在自己身旁,那個一直在身邊默默守候、跟自已一樣有愛心、行公義,好憐憫的計程車司機廖俊明,結局自是大歡喜的幸福笑容。
故事兩三句說完,好像也沒有進電影院看的必要,但怎麼會有資深影評人看完後滿臉淚痕,久久不能自己?而又有怎麼會有老練的片商,淡淡地說:「這是好片,但不合市場口味」?一部愛琳娜,兩種極端的評價。
就結局來看,〈愛琳娜〉是喜劇。當然囉,在這麼悶的時代,拍喜劇是應該的。但是這部片看完之後,我們找不到哪個梗是所謂的笑點,哪些對白可以讓觀眾笑翻天。的確,沒有哪個角色在講笑話,或者精確地說,沒有一個角色的對白或動作,是在取悅觀眾。甚至,這部片還安排了演藝圈忌諱的「社會衝突」,毫不避諱「挫折」,女主角本來的期待最終「完全落空」,這怎麼會是喜劇?
其實,〈愛琳娜〉是一部「關於救贖的寓言」。在這部戲裡,喜悅與幻滅的元素是以隱喻的方式呈現。導演林靖傑安排了幸福童話故事中少見的社會抗爭,卻又在寫實近乎紀錄片的敘事中,安排了突兀的蒙面俠蘇洛(Zorro)式的角色,這些安排都是在指向一個生命的課題:「想要翻身的人,該如何翻身?」
有兩種解決模式。第一種:「攀附外力,藉機翻身」,這也是陳愛琳一開始的期待。不切實際的夢幻,讓她一度完全無感於家庭的其他成員的苦鬱,更別說正視自己身上,賺食人必有的高風險。但,事與願違,浪漫來得快也去得快,轉瞬間陳愛琳夢幻破滅,處境如此不堪,如同晚上美麗閃爍的夜景,天亮後竟然是噴著毒氣的石化工業。
外力無法攀附,翻身沒有僥倖,此時林靖傑向觀眾提出的第二種模式:「自立自強、自力救濟」。於是,陳愛琳手上的小提琴,從原本打算當做晉升上流階級的工具,轉換成對普羅大眾認同的禮讚。在樂音中,與其說陳愛琳安慰了嚎啕的小女孩、振奮了無援的關廠女工、改變市儈的才藝班老闆,不如說是這位蒙面女俠以極富侵略性的控弓、跨弦技法,驚醒了自己。琴弓如劍,所指之處,「斷開魂結,燒毀網羅!」
是的,非得要用此種高強度、超現實的姿態,才能展現走第二條路的毅然決斷,也非得要在「生活現實中自我瘋狂」,才能闡述由此「瘋狂表現後自我實現」的覺醒。林靖傑的〈愛琳娜〉,以此種姿態展現一種佛教式的終極命題:「不假外求、不捨世間、找回本我,即身成佛」。這是這部寓言影片的終極關懷,明白這點之後,就知道一般所謂的商業喜劇、賀歲大片,只不過是個鬧劇。
若放在台灣現在這個時空來看,〈愛琳娜〉並不只是個愛情故事,做為一部寓言,這部片也隱喻了高雄以及高雄人。這當然不只是這部片大部分都在高雄拍攝,而是,林靖傑所選擇的場景皆深具歷史意義,見證了從繁榮到沒落的滄桑。諾曼‧佛斯特(Norman R. Foster )設計的現代捷運車站,對照著正在拆除的破落眷村;一度供應全台農地化肥的硫酸錏工廠現在成了污染控制場址,徒留阿爸的嘆息與追憶。陳愛琳在貨櫃碼頭前述說著童年的回憶,高雄人看在眼裡,都知道愛琳童年時代繁華的高雄港,如今早就成了過去式。而一整排石化工廠,夜晚白天不一樣,愛琳娜在這痛哭被幸福「遺棄」,這種感覺,深受污染之苦高雄人最能瞭解,因為,高雄不就是台灣經濟榮景裡被「遺棄」的城市嗎?
隱喻不但在戲裡,也在戲外發生。台灣,好像是「一個國家、兩個世界」,同時住著少數的「天龍人」,以及大多數被壓在底下有難言、有志不得伸的「非天龍人」。林靖傑強調,他的〈愛琳娜〉就是為廣大的「非天龍人」拍的,甚至這部根植於南部台灣人心境的影片,若發生「非天龍人看了感動莫名」,而「天龍人看得莫名其妙」的情況,他也甘願。
導演如此執拗,不僅讓「天龍/人生勝利組」與「魯蛇」的意識型態,在劇中拉扯,也在這部片子的行銷上呈現。台灣國片環境的慘況,路人皆知,長久以來沒人把拍國片當做一回事,直到魏德聖的海角七號獲得驚人的成功後,商業界才開始重視國片導演的努力。林靖傑的〈愛琳娜〉在2009年台灣棒球隊在二連敗於中國隊之後的苦悶社會中,構思籌劃;而在魏德聖史詩,〈KANO〉,一部喊出南台灣熱情生命、觀眾票選最佳影片、卻在2014年金馬獎彷彿不存在的大眾錯愕中,殺青完工。而今,國片的環境依然艱苦,發行片商的選擇權柄仍然是影片是生是死的最高判準。林靖傑決定自己發行、自己宣傳,不讓自己的苦心被草草打發。影片的最終上演了「魯蛇的逆襲」,這些被天龍人忽視、輕視、蔑視、大部分時候被視作是魯蛇的「非天龍人」,最終成功地展現了自我,被看見、被承認、被愛。而,這會是〈愛琳娜〉票房的「自我實現預言」嗎?
誠如人的覺醒終會有時,觀眾也並非鐵板一塊。我們期待這部片子,最終不只讓「非天龍人」窩心,也能讓「天龍人」幡然覺悟,成為「前天龍人」。屆時,台灣不再是兩個世界,而得能血淚交織,一同哭泣、一同歡笑,這應該是這部片的期待與關懷。
但,一個天龍人真的能了解平凡百姓的苦痛嗎?
好吧,我們這樣說好了:就算你是個不折不扣的人生勝利組,自幼成長於台北天龍國,但,當你看到司機廖俊明驚聞愛戀的女生已經跟別人「好了」,而且還「有了」,忍著淚水,在如流水的車潮中汨汨泅,不知何去何從時,當你也為這一幕動容,隱隱心痛,甚至想拍拍他肩膀給他打氣,給他一點安慰,此時,
你,其實已經不是天龍人。
作者:李重志(青平台基金會副執行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