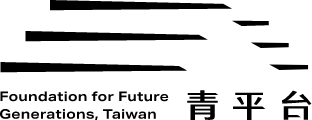【講座紀實】攝影背後,看得見與看不見的國際志工倫理

由青平台主籌成立的作伙國際志工交流平台,於 4月29日晚間於慕哲咖啡廳地下沙龍,舉辦「瞧!這些國際志工!:觀景窗背後的省思與對話」交流講座,由資深海外工作者賴樹盛擔任主持人,邀請願景青年行動網協會主任簡嘉信、國合會駐聖露西亞長期志工鄧雅蘭,與《視記》影像平台共同創辦人潘人豪,共同從攝影事件切入,談國際志工中的權力倫理關係。
作伙國際志工交流平台於2015年1月成立,由一群對於國際志工有興趣的朋友組成倡議、交流組織,平台成員從對國際志工有興趣的學生,到國內外志願發展工作者,每月共同聚會討論相關議題,並舉辦「國際志工再定義」系列講座,與社會大眾共同對話。
於 4月29日晚間首登場的「瞧!這些國際志工!:觀景窗背後的省思與對話」交流講座,打破一般的單人單向演講方式,邀請三位不同背景的國際志願發展工作者,從不同的角度分享經驗與想法。
重點不是看見了甚麼,而是看見之後的選擇。
曾帶領超過一千位志工到海外服務的簡嘉信,回憶過去九年來的服務經驗,對於國際志工倫理議題特別有感觸。
「如果你無意間打破隔壁鄰居家的窗戶,你會怎麼做?」嘉信首先拋出這個問題給觀眾思考。正當大家仍思索答案時,嘉信以紀錄片《中途島》分享他的想法:位於太平洋之心的「中途島」,人跡罕至,是信天翁候鳥的棲息地,但攝影師克里斯喬登(Chris Jordan)第一次踏上中途島卻發現,隨處可見的信天翁屍體裡都是太平洋飄來的塑料垃圾,甚至有打火機。「根據黑潮基金會的研究,島上14%的打火機都來自台灣。」嘉信指出,其實有許多我們無意間造成的傷害,透過國際志工,也許正是我們彌補這些無心之過的方法之一,也是讓「人們有意識地活出『人』應過的生活」。
嘉信分享他第一次意識到志工攝影倫理的經驗,是曾引起軒然大波的攝影作品《飢餓的蘇丹》(The Starving of Sudan)──一張蘇丹內戰地區,禿鷹虎視眈眈看著小女孩的照片,讓自由記者凱文卡特(Kevin Carter)得到普立茲獎,但隨之而來的,質問卡特怎麼沒有解救小女孩的輿論壓力,讓卡特無法承受,在得獎兩個月後自殺。
嘉信回憶,當年他很輕易地接受了媒體的資訊,卻在多年後發現,當時那位攝影師其實有將身上的乾糧與水給了小女孩,並趕走禿鷹。「我們太容易滿足於別人給的答案,忘記停下腳步思考真實性。」而此照片其實引起了世人對於蘇丹內戰的注意,攝影師成功地藉由一張照片,凸顯了議題。
但回到帶領國際志工的經驗,嘉信也承認有些志工的攝影其實是「為了自己」
──時常在照片中,發現志工本身是主體,當地人成為了裝飾性的「背景」。讓這些一次性志工看見他們未曾發現的,包含志工服務倫理,嘉信認為是國際志工推動組織的重要任務。
在願景的服務地點菲律賓奧蘭哥島,有幾間鄰近志工宿舍的雜貨店,每次因志工的到來與消費,都能大賺一筆,間接造成其他較遠的雜貨店產生「相對剝奪感」,甚至有幾家雜貨店因此倒閉。嘉信將這個觀察,分享給團隊的志工,讓他們注意到這些看得見與看不見的細節,也邀請志工一起做出改變,到較遠的雜貨店消費,給予公平的機會。
「重點不是你當下看見了甚麼,而是你看見後做出的改變。」嘉信認為志工的攝影只是一個媒介,看見現象後做出的改變,才是國際志工重要的倫理。
文字與照片都是說故事的權力,審慎地運用非常重要。
鄧雅蘭在前往聖露西亞擔任長期海外志工前,也曾在國內幾家NGO服務。
當時她在組織內招募志工,她總是告知志工相關攝影倫理:須徵得對象同意,且不得上傳網路平台。後來當她到海外擔任公衛相關志工時,也謹守這些攝影倫理。
雅蘭在服務時鮮少拍照,除了一些必須製作報告而用的照片,她也會與被服務者溝通過才拍照。一次,雅蘭在結束家訪衛教時,步出社區長輩的家,看見這棟房子位於段崎嶇的山坡路上,有感而發地拍了老人的背影與他的房子,同事看到了雅蘭的照片,告訴她:「這是別人的家耶!妳為什麼可以這樣拍照?」。這次經驗讓雅蘭了解到,被服務者對於隱私界線是比拿起相機的我們更有意識的,不應因為自己是服務者,就認為自己擁有對他人拍照的權力。
因為自己看待攝影的嚴謹態度,讓雅蘭驚訝於國內推動國際志工時,許多單位都將被服務者的照片印成明信片,甚至是大大的海報,搭配「愛心」、「落後」、「貧窮」等文字,無意間加深了服務者高高在上,被服務者地位低落的刻板印象。
「照片之外,文字也是很重要的說故事工具,必須審慎地運用。」雅蘭分享她初到聖露西亞的社區健康中心工作時,看見自己的同事每天下午2點就開始午休,認為他們很「懶惰」。但後來才發現,原來聖露西亞人非常重視家庭,女人每天早上3點就起床做家事,燙衣服、洗鞋子等,也因此到了下午才會這麼疲累。
同事們後來也反過來問雅蘭,為什麼她的衣服總是皺巴巴,鞋子總是髒髒的?雅蘭這時才發現,原來她在自己同事的眼中,才是「懶惰」的人。她也意識到,如果自己沒有先理解背後原由,就將照片和文字分享出去,就會造成他人認為聖露西亞人懶惰的錯誤印象,因此照片和文字的運用,都需要更加謹慎,避免落入單一故事的危險性。
對雅蘭來說,志工倫理,最重要的就是同理心。我們是否能夠在服務對象的立場思考及省思,了解看見對方,而不是用自己的想要卻掠取或給予。拍照也是一樣的,我們總不希望自己的國家與落後畫上等號,不希望自己只是單純的穿著簡單出門,卻被認為「貧困」。
了解鏡頭背後 ,自己的角色與定位,就不會踰越。
潘人豪除了是《視記》平台共同創辦者,同時也是海外醫療資訊系統技術的專家,熱愛攝影卻又是國際技術交換專家的他,時常面臨「角色衝突的解離」。
人豪時常為了收集醫院相關資料,必須在院內拍照,而他在拍照前,通常不會在乎畫面中的病人或醫療人員的感受,認為這些照片是為了「反映事實狀態」。但一次在攝影過程中,一位當地婦女對著她高舉雙手並大喊:「不准拍!」讓他反省,這樣的心態,實則顯露了自己「知識的傲慢」,以為為工作而紀錄的照片,就可以忽略被攝者的感受,也許他有其他更好的取得照片方式,例如請院方代為協助拍照等。
而人豪認為,海外地區發展首要任務就是幫助對方建立「商業模型」,將技術轉移給對方後,他們能夠獨立持續運作,才是實質的幫助。專業者分享技術時,更要富有同理心,把對方當成自己的伙伴,而非受援助者,才能避免落入「知識的傲慢」。
熱愛攝影的人豪,一次面臨了「想拍,最後卻沒有拍照」的天人交戰。2014年海地地區爆發霍亂疫情,當時的霍亂病房滿是病患,擠滿架上、床上和地上,帶有傳染原的排泄物也無法清理,流滿病床的地板。當時要與院長共同商討解決辦法的人豪,面對眼前難得的景象,極為想拿出相機記錄,但經過一番內心掙扎後,他決定還是要回歸專業工作者的角色,忍住攝影的慾望,專注與院長討論解決辦法。
「了解在鏡頭背後,自己的角色與定位,就不會踰越。」人豪認為當面臨志工倫理時,釐清自己的角色與定位,就不會有踰越專業或倫理的行為。
在三位與談者各自分享經驗與看法後,主持人賴樹盛也個別針對他們的分享提問:
Q1:「若遇上志工以獵奇方式恣意拍攝,嘉信身為機構工作者,會如何處理?再者,願景青年行動網協會及當地合作單位是否有相關志工規範呢?」
嘉信認為組織可透過志工訓練敘明原則與建立心態,但並非每一位志工在第一次經驗中,就了解自己的角色與守則,因此應給予學習的空間和機會。這時,組織與在地社區就必須事先溝通,達到共識,讓社區居民理解志工狀況,才能避免志工違反倫理而產生的誤會。
而願景的其中一項志工規範,是關於「物資發放」──願景希望志工發放物資應有一定的原則,如孩子表現好時作為一種獎勵,而非漫無限制地發放,養成孩子對於志工角色就是物資發送者的錯誤期待。
一次,嘉信在奧蘭哥島社區遇到兩位韓國觀光客,他們到雜貨店買了許多糖果,邀請社區的孩子們呼朋引伴來領糖果,嘉信看見這樣的情景,立即上前溝通,讓韓國志工了解這樣的行為可能造成的影響。
Q2:「當雅蘭在海外服務場域裡,為了服務工作目的進行拍攝,是否皆能真正反映對方當事者意願?作為公衛推廣志工,妳所提供的服務影像是否能反映出當地公衛問題根源? 再者,派遣組織及服務單位又是如何看待或運用你服務工作影像?」
雅蘭分享,自己在聖露西亞健康中心的權力,事實上不若想像中高,因為當地人認為,醫生和護士都擁有較崇高的地位,而雅蘭僅是「志工」,加上外表看起來較為年輕,因此當地人若不希望被雅蘭拍照時,就會直接地拒絕。這也反映了攝影者與被攝者之間的「權力關係」,會影響當下的情境。
而雅蘭拍攝的工作照片通常是為了每季的報告使用,後來較常作為原派遣單位「招募志工」時使用,也因此照片中的當地公衛問題反而並非主體性,志工本身才是畫面的主體。
Q3:「人豪作為一位海外技術合作專家,假若當贊助機構以其他目的(如政治、外交等),要求你以影像記錄進行官方宣傳,甚至要求當地服務對象配合演出,你個人如何感受?又會如何處理?」
人豪表示,如以結果導向,這些影像能夠讓他們取得更長久的合作與贊助關係,讓社區得以發展,且過程不違法,就可以接受這種「必要之惡」。影像紀錄本來就有「行銷」的目的,透過適當包裝,但仍真實地呈現當地的問題與需求,不僅可以吸引人,也可以反映現實。
而賴樹盛針對這個問題也分享自身經驗:一次有大人物來訪泰緬邊境的學校,在校方活動開始前,就先召集大家與大人物拍照,而大人物拍完照後旋即離開,在沒有任何事前的溝通或互動下,他們優先處理了拍照的需求,流失對他人的同理心。
嘉信也分享,願景時常有與學校合作的團隊,老師為了報告與核銷,勢必有要求服務對象一起拍團照的需求。這樣的需求沒有錯誤,但應拿捏適當的時機點,以不打擾對方一般作息,尊重對方為原則。
針對主持人與三位與談人的分享,現場觀眾也提出一些問題作討論:
Q1:「大多時候都是志工拍照並用文字記錄寫故事,但有沒有機會換成當地人說他們的故事?」
一位服務於以立國際服務的觀眾分享,他們曾規劃過「將相機交給當地人」的計畫,讓他們有機會用相機說故事,透過他們的觀點,呈現出在地故事。
人豪則指出,這就是讓對方擁有「所有權」的作法,先由當地人講出自己的故事,闡述自己的需求或看法,服務者可再分享自己不同的觀點,讓被服務者也意識到,原來還有不同的觀點與想法,原來自己可以做到更好。
而賴樹盛則表示,服務過程中應「互為主體」,不只是單向地從志工自己的角度出發,「其實許多被服務者都有豐富的『被援助的經驗』」,也許他們能說出許多精彩的故事。
Q2:「在製作宣傳影像時,如何克服達到宣傳目的,與畫面讓當地被貼標籤的兩難?」
嘉信表示,宣傳前應考量畫面吸引力與故事的真實性,願景的宣傳照片通常呈現當地純樸快樂的一面,鮮少選用悲慘、貧窮意象的影像,而這也是當地居民平時呈現給志工的樣子。幫助沒有辦法傳遞故事的人傳遞,嘉信認為志工的照片有時反而反轉了一般人對當地的刻板印象。
又以願景宣傳團隊志工計畫所用的文句「海外村落認養」為例,嘉信表示協會運用「認養」一詞,其實是從中性化角度看待,代表「把這個區域當作自己責任範圍」之意,但部分大眾仍會認為不妥,也因此在字句使用上,必須更小心斟酌。
柬埔寨垃圾場童工旅行團,透過攝影看見議題
講座的最後,主持人賴樹盛分享了「柬埔寨垃圾場童工旅行團」的新聞。賴樹盛認為,雖然此行為受到許多輿論,但是透過這個旅行團,讓大家看見當地的垃圾問題,讓參與者思索,找到自己可以改變的方式,也許這些本來製造許多垃圾的外國觀光客,會因此開始將垃圾減量,或是更加環保。
人豪也提醒大家,應練習從大環境、長程來看每一個問題與事件,若藉著傳播影像能達到解決問題的目的,問題成功被解決才是重點。志工應跳開自己的角度,宏觀地思考問題的本質,達到解決問題的目的。
嘉信最後則分享,一如電影《貧民百萬富翁》上映後,也掀起了印度的貧民窟觀光潮,反映現代人接受太多數位媒體資訊,一窩蜂地跟從卻缺少了自我省思。而不管是在觀景窗的前方或是背後,看見之後的「選擇」,才是國際志工應思索的重點。
本次交流講座吸引96位觀眾,將近三小時的精采討論,透過賴樹盛、鄧雅蘭、簡嘉信和潘人豪的分享,讓大家重新思考平時未曾注意的攝影與志工倫理,有了不一樣的省思與對話。
作伙國際志工交流平台,持續舉辦相關志工交流講座活動,5月14日晚間舉辦《國際志工再定義》第2場系列講座──「田野中的自我認同:海外服務中的衝突與適應」,探討海外服務者自我認同的重新建構過程,是國際志工的重要成長課題。邀請每位有興趣的朋友,再一次展開對話與交流。
特別感謝 活動志工:
統籌、網宣設計:陳昱廷;服務台:朱令儀、謝昀軒;記錄:曾彥菁;電腦、音控:吳奕辰;錄影:陳貞攸、盧有恆;攝影:黃一中、陳昱廷;網路直播:葉俐伶;機動:王詩菱
作者:曾彥菁(作伙國際志工交流平台成員;VYA願景青年行動網協會執行秘書)
文章來源:無
發表時間:2015-0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