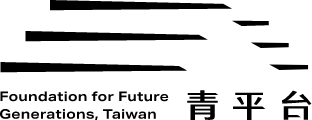【講座紀實】愉悅重生,或痛不欲生?

「當海外志工在田野中,遇到當地文化與普世價值或個人價值有所衝突時,志工應如何適應與改變?」
由青平台主籌成立的作伙國際志工交流平台策劃的《國際志工再定義》系列講座,於5月14日晚間再度登場。以「田野中的自我認同:海外服務中的衝突與適應」為主題,討論志工於服務的過程中,可能遇到的自我認同混淆,進而產生衝突或改變。由中國環保組織志願者林吉洋擔任主持人,台大社會學博士趙中麒為主講人,並邀請曾任不同國際組織志工的平台成員朱令儀、王慧思與洪翠苹分享他們的經驗。
分離、轉變、再重組
曾以泰緬邊境族群議題為研究主題的趙中麒博士,有多次深入田野採訪的經驗,對於志工於面臨異文化衝擊的自我認同,有著深刻的見解。
他認為擔任志工的動機,並非因為志工身分帶來的光環,而是進行一種生命儀式。
在出去接觸外部世界以前,自己的價值觀,與對世界的認識,都是在原先身處的社會與環境中型塑,因此當他首次接觸到外部世界,接受到不同觀點的相互衝擊與矛盾時,可能是相當痛苦的過程,如同人類學中的「Liminal Phase」,意指儀式中的人脫離了原來的身份,又未曾達至完成儀式後的新身份,是身份、角色、自我意識、對外關係都難以確定的尷尬時刻。也是一種象徵性的死亡與重生。
而這樣的生命儀式,共會經歷三個階段:分離、轉變與重組。
- 分離(Separation):當志工前往海外服務前,他必須與家人、朋友分離,更重要地,他是與過去的生活、人際關係等分離,準備開始不同的生活。
- 轉變(Transition):當志工於田野中發現與自己過去生活經驗完全不同的文化,甚至是與自我價值觀相衝突的當地文化,讓他開始產生自我認同混淆。這也是心理最痛苦的時刻。
- 重組(Reintegration):志工於適應與思索後,開始「部分重建」自己的價值觀,但仍保有自己原有的價值觀。
趙博士以幾個例子與大家分享:如面對「以手吃飯」和「原住民輪杯」文化時,志工可能因「現代化教育」中的公衛知識,認為可能不衛生或有傳染病的風險,而在心理上產生抗拒。又或者,前往擔任志工的地區,是一個較晚步入「現代化」過程的部落社會,聽他們的長者講古,提到他們以暴力行動驅逐進入他們部落領域的人,這種行動,發生的時間可能距今不遠,當他們講述的時候,仍可以感覺到他們的血液在沸騰。他們的做法,或許會和我們的和平價值觀牴觸,但那是「那個時代」捍衛傳統領域的方式。
愉悅重生,或痛不欲生?
當發生自我認同衝擊時,希望自己死狀悽慘或優雅殞落?是踰越重生,還是痛不欲生?
趙博士認為有三個原則,可以幫助我們的重生過程更加順利:
- 共融與入境隨俗(Rapport and Go Native):避免用自身既有價值判斷田野中的人事物,如有些文化中沒有私有財產的觀點,或是以手吃飯等。盡量用當地人的角度理解當地文化,但並非追求變成當地人,因為這是無法達到的。而閱讀相關資料,能促進文化差異的理解,也能幫助我們避免用自身價值判斷當地文化。
- 接受普世價值與文化差異的衝突(Culture shock and identity disorientation):認知到田野中必將面臨到價值衝突與文化差異的事實,但在尊重文化差異時,或對特殊價值的立場與態度,應有自己的思考,避免總是落入「這是他們的文化與社會,我尊重。」的廉價教條式主義。
- 不斷自我重建(Self-reposition):自我認同重建並非完成後即一勞永逸,當志工每每面臨到不同的文化衝擊,可能就會再度產生重建的過程,因此這是不斷變動的過程。
禁絕情慾或回歸人生
志工在田野中,可能面臨到的另一難題就是「個人情慾」──是否可以與當地人談戀愛或是有親密關係?或是應禁絕自己的情慾?
趙博士認為,志工應先了解每個社會自己的性別文化與界線,例如他曾於泰國進行博士研究時,其中一位研究對象於吃飯時幫他夾肉,並展現微笑,他知道這在當地文化中代表對方「有好感」的意思。而他知道自己兩週後將離開,無法接受進一步的交往,當時自己馬上就幫在場所有人也夾菜,化解掉尷尬。
又如美國人類學家肯尼斯.古德(Kenneth Good)36歲時於亞諾馬米部落(Yanomami)進行研究,並娶當地15歲女孩亞瑞瑪(Yarima)為妻,在1980年代也引起許多關於人類學家是否可以與研究對象發展關係的討論,「情慾研究方法」,這種透過婚姻關係變成局內人(insider)的研究策略,也一直存在爭議。
趙博士認為,不論在田野中選擇禁絕情慾,或是回歸天性,順應情慾,選擇後是否準備好接受別人的檢視與評判,才是重點。「如果你沒有準備好和當地人在一起,就請將褲襠上的拉鍊拉緊。」
尋找自我認同是一個持續的過程
擔任與談人之一的朱令儀,有著特別的成長背景,從小在泰國、英國和台灣等不同國家長大,讓她在哪裡都被當「外國人」。也因此對於尋求「自我認同」更有深刻體驗。
大學時期,令儀曾到育幼院擔任志工,陪伴小孩。一天,她看見因為有幾位善心人士帶玩具要發給孩子們,孩子們竟然自動地回到房間換上漂亮的衣服,並嚷著”It’s show time!”讓令儀發現,身處育幼院的孩子,在各種情境下,其實沒有選擇。
有一次,她聽見有一位年紀最小的孩子在房間哭,發現他是因被老師處罰,臉上被針扎出一道很像鬍子的痕跡。她很難過自己只是「志工」的角色,無能為力改變當下的情況。
或是另一次,令儀發現育幼院廚工的智障兒子,與院內的孩子有很多親密的接觸,並且教導他們一些有關生殖器的詞彙,令儀認為不妥,馬上反映給育幼院人員,當時院方就暫停了煮飯阿姨的工作,卻間接影響到院內的孩子只能改吃便當。
對於志工角色無法改變現況,或是試著改變卻影響到當地原有的生活,令儀仍然不知道最佳解為何,卻一直將這些故事放在心上,時時提醒自己在現在的工作岡位上,能有多一點的思考。
對於擔任志工時會面臨的自我認同衝突,令儀也有一套標準作業流程(SOP):旅程、感受、震撼、掙扎、行動。在旅程中感受到差異與震撼,可能一開始會掙扎,而想替事情找合理的解釋,到最後理解並展開不同的行動,令儀認為這個過程其實就跟冥想三步驟(體認、查覺、接受)相似,而這在志工旅程中都是持續不斷的過程。
令儀認為,志工的自我察覺應回歸到「人」:觀察自己如何理解與傾聽,對象如何同樣地感覺自己,是持續的功課。志工應保持清醒的自我意識,無論對錯,都對自己誠實。若因自己無法採取行動而無助時,仍要原諒自己,在自己的位子上仍持續做自己相信的事情。
工作與生活的文化衝擊,每天都在熟悉與遙遠當中拉扯
過去在中國《綠色和平》及《樂施會》工作的王慧思,曾遠赴祕魯《婦女與社會組織》擔任志工,他分享了自己在不同文化與組織中工作的經驗。
其實慧思未曾視自己是「國際志工」,對他而言只是在不同環境,做自己本來從事的非政府組織工作,出發動機也是因想看看有別於以往服務的國際型大組織,較本土的組織型態有何不同。
慧思第一個感受到的就是工作文化的差異,他上班第一週發現辦公室都沒有人,同事都出差去了,辦公室只有他和實習生,且因為組織人很少,幾乎所有人的職稱都是管理階層,跟以往在《綠色和平》或是《樂施會》科層式的組織架構差異甚大。
祕魯該組織的工作方法也不相同,慧思當時被指派要建置一個線上課程的網路平台,但是組織過去沒有建置網站的相關經驗。資訊背景出身的慧思,過去受到的訓練都是該先從使用者調查開始,再逐步釐清網站應該有的功能,但服務的組織因為資源和自身能力的原因沒有落實該步驟,直接就開始建置網站,讓慧思覺得不可思議。最終網站還是建置完成,但他也不清楚後續的運營情況。
除了工作文化的差異外,在日常生活中,慧思也感受到與秘魯文化與華人文化相似與差異之處。
當地的公共交通系統以小型巴士為主,無固定路線或站牌,只要看見有車經過就可以招手上車,車掌直接身兼售票員。剛開始不太適應的慧思,經過兩三次的嘗試後,體驗到這種隨興的樂趣,時常搭乘小型巴士到處走。
另外一個有趣的部分是飲食文化。在庫斯科(Cusco)一帶是高原地形,容易產生缺氧,緩解高山缺氧症狀,在他國違法的古柯葉,在當地不僅是合法的,而且是嚼食和泡茶都是傳統文化的一部分。而天竺鼠也是當地有名的傳統美食,有些人認為這種飲食文化很野蠻,但其實在西班牙人進入祕魯殖民前,當地其實沒有牛肉,以天竺鼠為主要的肉食來源。「只要了解文化現象背後的原因,就可以理解他們。」
但其實秘魯當地有很多華人,因此也有與中國文化相似的飲食,例如有許多「本土」中餐廳,提供經過秘魯本土化之後的中國菜,口味類似,但還是有大差別。反而在秘魯菜裡,可以吃到很多中餐的味道。「原本遙遠的距離,馬上被熟悉的感覺所取代,每天都是在熟悉與遙遠中拉扯的狀態。」慧思回憶那段在秘魯服務的日子,真是別有一番體會。
慧思認為大家不必將志工角色看得過重,只是換了一個環境工作,但因為背後可能有其他資源挹注,所產生的「權力關係」讓志工不能太隨意地扮演這個角色。志工不必想一定要「改變」,這是一個互相學習而產生改變的過程,幫助志工認識自己。
在台灣也會有文化衝擊,抱持向對方文化學習的心
曾參與印尼搶救熱帶雨林專案、菲律賓原住民聯盟志工的洪翠苹,回台後曾參與八八風災災後部落重建工作,感受到同樣在台灣,也可能會有文化衝擊。
森林系背景出身的翠苹,在學習過程中歷經「原住民是生態殺手」到「原住民是生態守護者」的轉變,論述上的轉變在實際進入田野後,才發現現況可能是複雜而多元、游移在光譜兩端間的動態。
一次,她跟著部落的叔叔一起上山,當戴著頭燈的叔叔發現水鹿時,叔叔非但沒有獵殺牠,反而用石頭丟牠,叔叔說,這隻水鹿太笨了,要讓牠知道,下次看到燈,要提高驚覺性。叔叔又繼續說,有時,其實很不想打太大型的動物,但身為一位獵人,負有餵養部落的責任,這些獵物不是他個人的能力展現,是祖靈要給他的,所以不能不打。這些經歷讓翠苹發現,獵人與動物間不全然是對立的關係,而獵人在自然中的定位及其與部落、與祖靈、與自然間的關係,其實是這個透過科學堆積起對自然理解的她,所難以用知識去明白的。
曾因為動物權而嘗試吃素一陣子的翠苹,在面對部落於各種重要慶典便以殺豬慶祝時,她總在一次又一次親眼觀看的過程裡,去一次又一次探索文明與非文明的辯證。翠苹自問,部落參與宰殺到烹煮的過程就比較不文明?那不知道食物怎麼來、送到眼前的食物都已處理過未見血的就比較文明?些衝擊都讓翠苹向對方的文化學習,重新思考與定義人與自然或動物的關係。
翠苹開始反思,自己對動物或自然的認識只是來自教科書,而非親身接觸。
而大學時期受女性主義思維影響的翠苹,對於女性自我意識有自己的想法,卻在部落經驗中重新思考男女互動方式與文化。在分享經驗前,翠苹強調她的經驗不是部落特有,在許多地方都可能發生,只是她剛剛好在部落遇到,也因為是在田野裡遇到,讓她重新去思考這些遭遇帶給自己的學習。一次,她被喝醉的叔叔「有意識地」抱住,當下她沒有反擊,事後向部落人反映時,他們只回應:「這就是我們與漢人文化的不同」,但翠苹自己內心清楚當中的「同與不同」。雖然那次翠苹來不及反應,在過去訓練背景下,她也對自己的「沒反應」感到氣憤,當下的她深刻感到「概念」與「身體」間的落差,而她問自己,還走不走這條路,既然要走,那就把這次的經歷當寶貴提醒,並開始練習對事件的反應,這樣下次再遇到時,她就更知道如何預防,或是如何面對這種衝擊。
「不要因害怕跌倒而開燈,而要因為跌倒才開燈」翠苹認為海外服務者面臨文化衝擊時,應專注在自己的路上,不因過分恐懼而關閉任何開放空間的可能性。
幫助自己打開世界觀,就已是對當地的助益
最後,趙中麒博士提醒,志工總是期待自己能給當地最好的服務,在服務的過程中也認為自己習慣的做事方式才是最好的,例如重視標準作業流程等,反而會讓自己陷入「專業主義」的迷思中。
在海外服務時,志工必搭四艘船(Ship):建立關係(Relationship)、朋友關係(Friendship)、信任關係(Trustship)、夥伴關係(Partnership),與當地建立良好的關係,是志工應該重視的課題。
千萬不要認為自己一定能幫助到對方,其實藉由志工服務,幫助自己打開世界觀,也許就已是對當地的助益。好比趙博士在泰緬邊境進行難民研究時,每天只能與當地人喝酒、聊天,沒有實質的幫助,但最後他的博士論文,卻讓人們開始關心這個議題,產生了不同的影響。田野倫理問題雖然沉重但不能迴避,因為每次志工服務的影響,將是長久的。
本次講座共吸引84位聽眾到場。作伙平台將於下半年持續推出系列講座,敬邀有興趣的朋友一起討論與思考重要的國際志工議題。
特別感謝 活動志工:
統籌:林吉洋;網宣設計:謝昀軒;服務台:賴樹盛、何之行;記錄:曾彥菁;電腦、音控:陳貞攸;錄影:范揚鑫;攝影:陳昱廷、黃一中;網路直播:葉俐伶;機動:鄧雅蘭
作者:曾彥菁(作伙國際志工交流平台成員;VYA願景青年行動網協會執行秘書)
文章來源:無
發表時間:2015-05-26